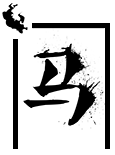下面的收文是由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同志Wen撰写,他在21世纪的前20年里一直活跃在中国的劳工支援工作中。其中大部分内容最初写于2020年1月,在2010年代最后一批劳工圈活动者被拘留,被迫进一步转入地下,或以其他方式被阻止继续进行他们以前关注的许多活动之后。然后,疫情把一切都搁置了几年。在过去的几个月里,Wen通过与我们的一系列对话,修订和更新了这篇文章,内容涉及原稿的叙述,以及在整个疫情期间涌现的各种形式的“行动者”活动和工人斗争,特别是在2022年和今年的最初几个月。
其中最近的一波无产阶级动乱从2023年1月开始,一直持续到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由退休人员带头,反对社会保险制度的改变——包括削减医疗福利和提高退休年龄的建议。我们认为,这一浪潮与同事发生的法国反对类似改革的运动大致重合并非巧合:两者都是对资本在全球推动削减社会再生产成本的回应,因为人口老龄化和经济增速持续停滞。这些分散的抗议活动似乎不太可能在国家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标准组合将其扼杀之前凝聚成一场全国性的运动,但这些和过去三年的许多其他斗争确实支持了我们的论点(最初在我们2015年的文章《前无进途,后无退路》中提出,并在随后的文章如《寻衅滋事》中更新), 即中国的社会再生产领域的冲突已经开始加剧,与传统意义上的 “劳工 “斗争重叠并泛滥。在这方面,中国自2010年代初以来的趋势与其他许多国家是一致的,反映了“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的深入展开。
就业方面的结构性变化引起了中国无产者政治主体性和随之而来的活动的类似变化。这种双重转变就是Wen文章中所探讨的劳工圈活动形式衰退的背景(这种形式在2000年代之前从未在中国出现过)[1]。除了强调这个背景,我们还希望进一步厘清我们如何理解产业斗争与劳工圈活动者之间的关系(Wen文章已经暗示了这种关系)。首先,这里讨论的那种专门的劳工圈活动者只直接参与过无数产业斗争中的一小部分,这些产业斗争大多是“自发”兴起的(尽管往往是由与活动者网络没有关系的战斗性工人组织起来的),贯穿21世纪的前20年。其次,正如另一位前活动者所说,“是中国工人(尤其是沿海制造业的工人)的集体行动吸引了活动者,并推动他们与工人一起前进,而不是那些具有不同背景和世界观的活动者推动工人的行动。然而,活动者……确实在工人自己的内部组织网络形成之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为[他们后来的一些]行动提供了基础”。
因此,这篇文章是对我们继续分析中国的群众斗争和左翼干预的一个重要贡献,也是对一种历史上独特的干预形式的讣告,其时代已经结束。与作者一样,我们希望对劳工圈活动者运动的坦率解剖能够为新的一代无产者提供教训,他们正在发起更适合当前条件的新形式的抵抗。虽然我们自己的立场和Wen的视角可能稍有分歧,但这篇文章是对中国阶级斗争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的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这篇文章为中文译文,英文原文见:The End of an Era: Labor Activism in Early 21st Century China(2023年4月)。我们欢迎读者的反馈,如果发现翻译错误、事实错误或不通顺的地方,或对《闯》网上发表的文章有任何看法,请和我们联系:chuangcn@riseup.net。
《闯》编辑
一个时代的结束: 21世纪初中国的“劳工圈”
Wen著
几年和几十年的时间流逝所创造的时间界限,很少与社会和政治变化的节奏相一致。然而,2010年代的结束似乎明确地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佳士工厂组织者和学生支持者的大规模被捕,2018年和2019年与佳士无关的劳工圈活动者的被捕,以及同一时期劳工团体、激进学生社团和活动者网络的关闭,以明显的悲观调调封存了这十年。我们知道,我们曾经如此熟悉的劳工活动者场景——参与者、组织、网络以及他们的组织目标和方法——已经蒸发,不太可能再回来。但是,这个场景到底是什么?
2010年代末的镇压
这篇文章的初稿于2020年初完成,紧随此前两年的无情镇压。原稿的重点是那场镇压、谁被逮捕、原因,以及这一切意味着什么,这反映了那个特定时刻的情绪和视角。值得保留的是,上述关键时刻催生了这一分析。
2019年开年,中国剩下的最著名的五名劳工圈活动者在1月被拘留(16个月后终于在2020年5月获释),这一年结束时,又有三人在12月被拘留(令人惊讶的是仅在15天后获释)。然而在这之间,其他一些劳工活动者,包括独立记者和社会工作者,在消失了几个月后,也加入了前几年被拘留的人的行列。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被拘留的人都被释放了——通常是悄悄地释放,释放的条件通常包括发誓保持沉默和切断与外界的联系。到2020年,这种任意逮捕(拘留时间同样任意)已经变得如此频繁,以至于如果几个月内没有人被捕,人们会集体松一口气。虽然我们难免猜测任何一次逮捕是否与另一次逮捕有关,但到了2020年,有足够多的此类事件让我们相信,任何个别案件的具体原因已不再重要了。
事后看来,2019年是一个转折点,这种新的国家镇压方式在这一年得到了巩固。警务工作变得更加先发制人,目的不只是为了惩罚活动人士的所作所为,还是为了防止他们接下来可能准备做的事情。随着每一层活动者被逮捕、审讯或严格监视,下一层活动者就会更加暴露,形成一个不断扩大的镇压同心圆。随后从2020年到2022年的两年更加证实这一趋势。2021年,至少有两名劳工活动者分别被捕,并被指控犯有更严重的“颠覆国家政权”罪。虽然自2019年以来,被盯上的活动者和组织的数量有所下降,但这反映的不是放松,而是新样貌的正常化,此时很少活动者能够以任何公开或有组织的方式采取行动。同时,在没有正式的警察拘留的情况下,无数的活动者和学生被带走,审问的频率更频繁。我们仍然处在2010年代末镇压的阴影中。
当这种镇压成为往事时,哀悼已经失去的东西是不够的。在我们能够继续前进并试图打造适合“新时代”的东西之前,我们必须首先厘清,在21世纪的前20年里到底是什么东西在兴起和衰落。一方面,2019年的逮捕标志着来自农村地区的农民工领导的工人斗争周期这个棺材的最后一颗钉子,这些斗争起初主要在沿海城市新的出口导向型工厂和基础设施项目中,但最终扩大到整个中国整个新兴的私营部门。这个由农民工主导的周期始于1990年代中期的零星劳工行动,在整个2000年代形成,并在2010年代初加强,而远在对活动者的最后一波镇压之前的2015年便开始解体—积极——因此,可以把这些活动者被镇压前的活动理解为是在为重现早些年阶级行动的积极性,而做最后努力。它的兴起恰逢另一轮工人斗争开始消退:城市国有企业的工人为捍卫他们的社会主义 “铁饭碗”而进行的斗争没有成功,斗争从1990年代初持续至2000年代末,2002年左右达到顶峰。界定农民工主导周期的不仅有其本身固有的劳工行动弧线,还有2000年代中期到2010年代中期出现、试图努力支持和指导工人行动的专门活动者和组织网络,以及某些关于允许做什么的想法、如何最好地组织(同伴)工人的假设,和对短期、中期和长期目标的理解。既然这个周期已经入土,而且还不清楚下一个周期将如何在目前的“政治抑郁”(过去几年中许多前活动者口中的短语)的背景下出现,我们有责任论述21世纪初农民工领导的工人斗争周期的情况,以此纪念这段时期。关于中国农民工本身的工作、生活和斗争已经写了很多[2],因此,这篇文章着重活动者的亚文化,这个文化及其团体从工人斗争中产生,有时还影响到工人的斗争。如此一来,我拒绝镇压主要是由习近平的专制人格驱动这个流行观点。相反,我想表明这一轮斗争有它自己的内在逻辑和节奏,与当时更广泛的物质趋势有关。
我们开始看到新一代的活动者在最糟糕的情况下挣扎着出现,他们没有过去的活动条件,也不了解发生过什么——但也摆脱了一些历史和意识形态的负担。在这一点上,我们也应该寻找未来的周期可能与前两个周期不同的地方。
一个周期的高峰
虽然这一轮工人斗争的起点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末,但抗争集中的阶段是2000年代中期延续到2010年代中期,仅有十多年。这一时期被寄予了极大的期望。2010年代的开端是2010年夏天的一次里程碑式的罢工,即被广泛研究的南海本田汽车零部件厂的罢工,其被广泛描述为代表了新中国工人阶级的成熟[3]。 随后很快就出现了一波汽车工人的罢工,同年晚些时候,大连工业区超过7万名工人的罢工可以说是为“工人行动年”画上了一个句号[4]。
在这些大规模的罢工之前,珠江三角洲的工人斗争多年来不断加剧,迫使国家在2000年代末通过劳工立法——按照国际劳工法的标准,纸面上是相当进步的——目的是为争取工业和平作出的让步。几年来,政府似乎至少在名义上站在工人的合法权利一边,而理由不过是确保其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社会经济基础获得支持。然而,回过头来看,本田罢工并不像当时许多人认为的那样,标志着工人的斗争从防御性转向进攻性、更加广泛和越来越有组织的斗争,而只是一个仍以防御性和地方性斗争为主的周期的高峰——这个周期在随后几年开始衰落。
在本田罢工之后的五年里,每年都有重大的发展,要么是大规模的、影响深远的罢工形式,在工厂之外有广泛的冲击,如东莞裕元鞋厂的4万人罢工(2014年);要么是激发公众广泛同情的劳工新闻形式,如富士康自杀事件(2010-2014)。工人和活动人士从来没有摆脱过骚扰和监视。暴徒被雇来袭击罢工的工人,警察定期骚扰和扣留活动人士进行审讯,劳工非政府组织(NGO)被迫搬迁办公室。但是,活动者们对这些新的发展做出了乐观和积极的反应,讨论如何更好地进行介入(工人行动)。国家试图通过立法和配套的亲劳工言论来平息劳工骚乱,显示出与劳工NGO合作的意愿,以这种权宜婚姻来获得工人对正在形成的、更加规范的劳资关系体系的认同。国家容忍劳工NGO的服务工作,同时以微妙或不那么微妙的方式监控和划定其活动的界限。
许多工人斗争的参与者和观察者认为,,必然会从大量的工人斗争中出现一个不断成长、更有组织的劳工运动,这其中不乏一些毫无道理的乐观主义。虽然经典的欧美劳工运动比人们通常认识到的更具有历史特殊性[5],但多年来,活动者、学者甚至中华全国总工会(ACFTU)一些改革派领导人在欧洲和美国的模式中寻找中国未来的道路。在2010年代初的抗争高潮时期,即使政治空间禁止任何自主的工会活动,也很少有人会完全排除工人发展出强大的工会运动的可能性[6]。相反,斗争的走向是开放的,它似乎可以有很多方向。人们确信,这不是一个“是与否”的问题,而是工人“朝着什么方向”和“什么时候”发展出强大的劳工组织形式。这种兴奋接近于一种必然规律的感觉,在今天可能很难回忆起,但它确实普遍存在了许多年。
活动者亚文化的三种类型
在这个周期中出现了两代活动者,他们被劳工行动所影响,并反过来影响了劳工行动。正是在2000年代末和2010年代初强有力的集体行动的背景下,中国一些最积极的劳工活动者(他们是2015年至2019年期间主要的镇压目标之一)几乎从头开始学习组织技能。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与前几代活动者隔绝,例如1990年代和2000年代初中国国有工厂的积极工人,他们中的一些人因为在抵制私有化和倒闭中的角色而面临特别严厉的镇压。这些新活动者中的第一批人是在1990年代末国有企业工人的斗争逐渐结束时出现的。后来的一代则是在2010年代初出现的,远在这些斗争失败之后。
新一批活动者远非同质化。我着重介绍其中三个具有鲜明特点的群体,他们在组织和试图建立劳工运动方面发挥了显著的作用[7]。
首先,第一代农民工活动者可以被称为 “草根农民工“群体,以深圳、广州和东莞等珠三角城市为中心,这些城市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仍然在快速工业化。这个群体的成员与此前农民工的背景大致相同,都是在这二十年间离开农村家乡到沿海地区工作。一些人建立了自己的劳工组织或加入了已成立的劳工组织,尽管许多人也作为无机构背景的组织者活动。许多人成为了中国新“劳工运动”的公众形象。他们很少有人受过大学教育,他们的组织大多由以前的草根工人组成,也有少数由大学毕业生组成。他们的意识形态往往是无定型的,通常将他们对工人利益的拥护与反专制以及亲市场经济的政治混为一谈,这在今天看来可能是不协调的,但在后社会主义国家却相当普遍。在那些政治上比较成熟的人当中,有一些把某种欧洲社会民主视为中国工人的理想未来,并普遍反对以专制统治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形式。许多人与对劳资关系感兴趣的学者合作,与同情他们的事业、愿意承担风险在适度敏感的案件中代表工人的律师合作。这往往将草根农民工活动者的亚文化引向法制逐步现代化,以摆脱国家干预,并引向以国际劳工组织(ILO)式的三方集体谈判为中心的劳资关系概念。尽管他们的政治立场温和,但他们的农民工背景、他们更加有组织的特质,他们通过国际基金会与外国资金的联系,以及他们新兴网络的广度,都确保了他们会被视为对国家的威胁。这意味着他们往往是镇压的第一批受害者。
第二类是“公民社会”群体。这个亚文化是由公民社会的发展形成的,它既是他们行动的概念框架,也是在广州占主导地位的现实——这个现实是从广州倾向自由主义的大学、商业化的媒体以及与跨境的香港公民社会活动者的联系中形成的。这些领导非政府组织的劳工活动者大多不认为自己是左倾或激进的,尽管在实践中不一定敌视有时给他们当志愿者的、左翼立场更明确的学生和工人,有时候还会和他们合作。他们同样赞同社会和政治自由主义,这种自由主义与2010年代初在省委书记汪洋领导下广东省政府的改革派转向同时兴起。许多人在当地大学上学时被政治化,通常是通过参与志愿者活动,接触自由主义媒体,或参与行为艺术和小规模示威等活动。由于环境更加宽松,他们有机会参加那些年的许多公民社会组织,与从事一系列其他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活动者形成网络。他们中的一些人最终会选择为这些组织工作,而另一些人则继续沿着学术道路前进,有时会与公民社会保持联系。
最后,还有一个首先主要在北京出现的“激进左派”团体。这个团体以明确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学生和应届生为基础,通常采取“学习小组” 的形式,深受国内一些精英大学中形成的某种毛主义的影响。这种毛泽东主义与其说是一个连贯的政治纲领,不如说是对毛泽东及其被认为进步和有利于工人的政策的怀念和捍卫。这些学生往往受到教授和老一代毛主义网络的影响,这些网络通常与失去生计并感到被90年代的结构调整欺骗的老一代国有企业工人有关,因此这些学生激进分子的意识形态训练通常先于他们的劳工活动。许多人在意识形态训练过程中,在更资深的学生激进分子的指导下,开始面向劳工组织活动。这些团体往往意识形态统一,纪律严明,经常进行工人调查(针对校园工作人员或附近工厂或建筑工地的工人),以此学习组织工作并建立学生-工人联盟。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以其意识形态上的异端和这些跨阶级的联盟对国家构成了双重威胁。但长期以来,他们的活动主要限制在讨论和一些初级的组织形式内,之后才被国家认真看待。2017年底出现了一个转折点,当时当局拘留了一些学生活动者,他们被统称为“左翼八青年”,在广州组织读书会并接触学生和工人(其中一些人为此从北京搬到了珠江三角洲,这里曾是农民工斗争的温床)[8]。 尽管他们后来显然因为党内左倾的前领导人干预而被释放,但这使马克思主义学生总体受到国家的关注。可能是由于他们在精英大学的根基(因为大学生通常比工人和非学生活动者受到更宽大的对待),一直没有发生严重的全国性镇压,直到2018年的佳士事件及其次年的后续[9]。从那时起,大学学生就受到紧密得多的监控。
劳工活动的主要组织形式是NGO,这个形式与中国早期的劳工传统脱节,在鼓励成立NGO的全球公民社会运动的高潮中出现,并且在国家压制独立工会的背景下。前两类团体主要在这个框架内行动。NGO虽然不完全同质,但从未发展成能与群众组织相提并论的东西,如历史上的工会或政党,我们也不应该期望会发展。
虽然“公民社会”和“激进左翼”团体在意识形态上有分歧,但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有一个共同的背景。他们都大致属于同一代受过大学教育、理想主义和坚定的年轻人。在2000年代末和2010年代初,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在广东和北京的中国最高级别大学就读。他们在精英大学的教育本来会给他们一个良好的生活起点,即使不一定是舒适和有地位的生活。但他们不一定来自精英家庭。许多人受到农村和移民家庭背景的影响,因此认同在工厂和建筑工地的无特权贫困农民工阶级。2000年代后半期和2010年代初新工人斗争的高潮——本田罢工和富士康自杀事件是两个关键事件——使这些学生进一步激进。然而,他们变激进时的所在(北京或广州),可能与使他们激进的内容(如工人斗争)同样重要。实际上,“草根农民工”和“公民社会”这两个群体之间也有相当大的重叠,尽管他们的个人背景非常不同,但他们以劳工NGO的形式占据了同一个政治空间。我提出这一点是为了强调,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团体之间的关系不断演变,有时会逐渐疏远,甚至相互敌视,而有时则是合作和保持联盟。
参与工人斗争的类型
为了理解2010年代末针对这些专业活动者和支援网络的镇压与中国更广泛的工人斗争之间的关系(这些活动者只参与了其中的一小部分,尽管这些斗争有时因媒体关注等因素而变得更加重要),借鉴Parry Leung在研究中国南方珠宝行业的罢工和劳工圈活动时发展起来的罢工类型学以及与每种类型相关的参与者的类型很有用处[10]:
第一类罢工——自发罢工:自发性质的群众行动,没有组织者或任何准备;缺乏战略规划,没有工人代表与管理层谈判。
第二类罢工——活动者领导的罢工(一次性的行动): 由少数劳工活动者策划和组织,并得到广大工人的支持;管理层和工人代表之间进行非正式谈判,但没有达成正式协议。劳工活动者或工人积极分子[11] 在罢工后不久就面临报复和解雇。活动者/积极分子的组织核心在罢工后通常会被解散或解体。
第三类罢工——活动者领导的罢工(有一个持续的活动者/积极分子核心): 罢工不是一次性的事件。领导罢工或抗议行动的活动者/积极分子核心以前就有发起罢工的经验。活动者/积极分子核心网络能够反复发起罢工行动或为其提供支持。活动者/积极分子核心是由“准领导 ”领导的。
第三类罢工可以进一步分为两个类型:
第三类一型——持续的活动者/积极分子核心是一个跨工厂的活动者/积极分子网络: 活动者/积极分子的跨工厂合作;活动者的组织结构在罢工行动后可以持续,但它在特定的工厂内运作。活动者/积极分子核心是由来自不同工厂的活动者/积极分子组成。
第三类二型——持续的活动者/积极分子核心维持在一个特定的工厂内: 罢工后,活动者/积极分子核心可以在工厂内维持和运作,通常在罢工期间选举工人代表,并在谈判后达成正式书面协议。
第四类罢工——领袖领导的罢工(目前在中国不存在): 一个有组织的劳工运动,跨工厂或跨地区的行动,促进工人的阶级利益,可以向工人群体陈述运动的明确愿景。运动领袖有决心将愿景付诸实践。
在这一轮斗争中,中国的大多数罢工似乎都属于前两种类型:自发的罢工和活动者/积极分子主导的罢工(一次性行动)。在某些情况下,它们可能发展为第三种类型:活动者/积极分子领导的罢工(有一个持续的活动着/积极分子核心),这种罢工维持着网络,但仍在一个工作场所内。正如Leung所指出的,最后一种类型跨越多个工作场所和地区,在21世纪初的农民工斗争周期中并没有发生(少数可能的例外,如上述2010年的罢工潮和2018年塔吊司机和卡车司机的全国性罢工——前者仅限于短暂模仿式的罢工,后两种情况反映了行业的独特结构,而不需要像其他行业如制造业那样的组织化)。
然而我认为,上文介绍的三种劳工圈活动者团体,以他们自己的组织方式,经历不同的成功和失败,都在试图建立最后一种类型的斗争,设想其为建立劳工运动的步骤,而不是一个不相关的罢工活动的集合。在最后镇压之前的几年里,“草根农民工”和“公民社会”团体专注于推广他们版本的集体谈判和工人代表制度(与其说是发明,不如说是一些NGO和劳工律师对工人斗争中新出现的趋势的一种采纳,在这些斗争中,工人发起了与管理人员临时性的谈判),以使工人代表正规化,虽然各种组织之间往往无法很好相处,但在广义上,他们正在成为一个网络,有大致共同的目标和方法。而“激进左派”组织在建立学生-工人联盟的过程中也变得更有组织性,他们不仅在大学校园里,也在工厂里发展自己的网络(佳士只是学生和其他左派活动者试图嵌入工厂的最著名的例子),从意识形态上将工人斗争激进化。
虽然这些活动者经常夸大他们自己在所有这些努力中的重要性和成功程度,但他们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这三个团体的活动者在更大范围内凝聚工人斗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把来自不同工作场所和行业的工人联系起来,让他们与其他地方的活动者和学生支持团体联系,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在短暂的罢工之间保留和传递经验,并指导工人的斗争策略。这些通过网络以有组织的方式凝聚斗争的尝试,在过去几年中成为镇压的焦点。这些网络确实已经被扫荡干净了。我不同意镇压只是习近平或任何其他国家领导人威权个性的结果。推动镇压的一个关键因素,以及对镇压时机的一种解释可能是这个:活动者的团体实际上正朝着将第二和第三类罢工凝聚成第四类罢工,也就是更接近于“劳工运动”的方向前进。
然而,这样的活动者太少了,无法将这些斗争整合成一个运动,而且他们从这些斗争中有机培养领导力——在工人自己当中——的记录一般都很差。活动者的团体仍然主要是“外部”干预的努力,这在佳士事件中变得很明显。为数不多的例外情况在他们有机会扎根之前就被消灭了。这反映了一种认识,即如果国家能够压制劳工组织者和组织,那么劳工叛乱本身发展成有组织运动的机会就会低很多。劳工研究的限制也越来越大,剥夺了讨论劳工组织战略的学术空间。
中国国家通常能够处理由工人单独组织的劳工骚乱,但对外部鼓动者特别警惕。然而,对劳工活动者的镇压并没有阻止工人的罢工,因为工作场所的组织很少主要依靠这些活动者。自整个20世纪90年代到现在,在农民工自发罢工和抗议活动中,工人很少被集体拘留[12]。部分原因是没有工会或其他组织领导罢工,那些已经存在的工人领袖往往是有机地出现,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而不是被正式选定,因此,当局识别他们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然而,只要当局确定的任何领袖也在他们自己的工作场所之外组织起来,他们成为强力镇压目标的机会就会大大增加——即使有时对罢工工人本身作出让步以平息罢工。
在强调这些活动者团体的时候,我并不是说他们代表了工人的斗争,或是形成斗争的最重要因素。毕竟在过去二十年里,中国的工人斗争并不依靠外部组织者来组织罢工。工人在自己的工作场所,通过个人和老乡的圈子进行动员,在集体行动中自我组织。这种自我组织,是今天更为去工业化的经济体里的劳工组织者所羡慕的,作为一种劳工与资本直接斗争的形式,不以工会官僚机构中介,,它是一种福气,同时在无法进一步巩固这些组织的情况下,也是阶级发展为有组织力量的障碍。尽管如此,活动者们还是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试图将斗争的循环推向特定的方向。
周期的结束
然而,这种工人斗争的周期到2010年代中期就已经结束了。这在当时并不那么不言自明。事实上,2013年和2014年发生了一些自2000年代初国有企业斗争以来最大的罢工,当时的学术论述谈到了从防御性工人斗争向进攻性的过渡。然而,中国的工业化(以工业就业人数占劳动力的比例来定义)在2012年左右达到顶峰,正好是工人斗争达到顶峰的时候,随后的去工业化明显表现为珠江三角洲等中心地区的制造业关闭,以及向内陆和中国以外地区转移。在这些事件中,包括一些大规模罢工的在内的工业行动的性质,,转为防御性,要求雇主提供更好的离职补偿和补缴养老保险。即使取得了胜利,这种行动也很少建立起持续的斗争。换句话说,2010年代后半期这种工人斗争周期的衰落和最终结束,是受正在进行的经济和就业结构性变化制约的。
希望和兴奋的十年很快让位于失望与绝望。在周期普遍衰落和结束的背景下,到2020年,镇压的浪潮已经席卷了所有三个团体。他们在2010年代初在不同程度上共享的空间,这个在其中学习和实践了行动的空间,在2015年后迅速消失了。2019年的逮捕只是标志着这十年来下行螺旋的高潮。其中一些早在2012年就有预兆,当时深圳政府骚扰房东,以迫使劳工NGO搬迁其办公室。尽管当时令人震惊,但当我们将其与后来发生的事情进行追溯比较时,这种间接镇压几乎是不值一提的,显然只是为了发出警告,目的是扰乱但不是阻止活动者的工作。2015年开始对劳工活动定罪标志着一个质的飞跃。
在对其他类型活动的镇压浪潮中,这种激化在2015年的最初几个月开始切实进行。首先倒下的是女权五姐妹,她们于3月6日被拘留,因为他们计划在两天后的妇女节发起行动,反对公共交通上的性侵犯[13]。随后从3月下旬开始,益仁平网络的活动人士被广泛扫荡(他们主要从事反歧视工作,但也雇用了同月早些时候被捕的一些女权主义者),7月9日,200多名人权活动人士和律师被拘留,最后在12月5日,广州的劳工活动人士首次被大规模逮捕[14]。 这些镇压在多大程度上互相关联?一方面,这些组织和网络之间的交叉融合可能促成了针对公民社会多个部门的整体性扫荡。 但是,对劳工活动者的镇压也有一个独特的背景,因为2014年和2015年出现了围绕缴纳社会保险和工厂搬迁两个主题的大规模罢工,由于工人的绝望和决心,这些罢工特别具有战斗性,而且难以化解[15]。 此外,一些劳工NGO介入了罢工,认为这是推动工人的声音在工业谈判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机会。在最初导致广州劳工NGO活动者被拘留的利得鞋厂罢工事件中,其中一些NGO曾帮助工人组织成一个准工会结构,并协助他们组织罢工,导致了几个月的持续抗争和与管理层的谈判[16]。这些劳工组织特意拒绝了地方政府和政府下属工会的干预。当时,中华全国总工会作为国家机构的一部分,在处理工人骚乱方面与地方政府密切合作,虽然试图获得工人信任并代表他们处理大规模劳动争议案件,却发现自己不敌与劳工NGO的竞争。
2015年的镇压开创了将基于争取权利的劳工活动入罪的先例,在过去,这些活动大多只是遭受警察的骚扰。2016年对三名劳工活动者的审判的影响一直回荡到2016年和2017年初,当时《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的出台使每个人对他们的安全更加紧张。(并非只有中国出台了此类法律以规管其理解的外国影响:大国中的俄罗斯于2014年出台了此类法律,印度于2020)。这部法律旨在阻止国际资金流向中国的公民社会组织(他们已经开始严重依赖这些资金),同时也为将来声称活动者的行动与境外利益有关创造了法律基础和政治合法性。该法于2017年1月生效。同年,三名隶属于中国劳工观察纽约总部的工厂调查员,在调查一家为伊万卡·特朗普品牌生产的鞋厂的过程中被短暂拘留[17]。 这一事件一度引起了人们对工厂调查被入罪的担忧,许多中国境内外的劳工团体都在进行这种调查,以收集有关工作条件的信息。年底,北京和其他地方的大规模拆迁以农民工为目标,此时协助被拆迁农民工的团体和个人本身也受到骚扰,并收到当局的严厉警告[18]。 大约在同一时间,上文提到的八位青年左派被拘留或被迫藏匿。这是对学生激进分子的第一次大规模镇压。这十年以镇压深圳佳士工厂组织者及其在全国各地的学生支持者而告终。这场镇压从2018年夏天开始,一直持续到2019年年中,裹挟了数百名各色活动人士和左派,包括许多与佳士事件无关的人。
除此之外,在过去的几年里,其他劳工团体以更安静的方式被关闭和压制,因为没有逮捕,所以也没有引起公众很大的注意。直到几年前,活动人士除了受到警察的骚扰和审问外,面临的风险相对较低,现在则面临着拘留数月和刑事审判的严重威胁,这急剧增加了任何从事活动的人的风险。在2020年和2021年数量有限的案件中,指控也全面扩大到更严重的“颠覆国家政权”。这还不包括许多因抗议活动而经常被拘留的工人,他们被拘留的时间长短不一,但一般不会被审判,而且我们极少得知他们的名字。2015年之后的每一年都让人越来越感到窒息,感觉事情越来越糟,没有任何希望的迹象。
国家的基本治理方法似乎在2014年和2015年左右发生了转变。在那几年里,政府很明显不再有兴趣与权利团体共舞,也不再有兴趣提供足够的渐进式改革来维持人们的希望。被认为是不可阻挡的政治自由化进程,被证明是国家治理中国的方法演变中的一个过渡期。许多关于这一转变的论述都指向2012年后胡温政府向习近平政府的过渡。这种叙事将大规模的政治和经济事件归结为以政治阴谋和政治家谋略为焦点,是书写中国历史和当今中国政治主流报道中的一个常见套路。这种过度简化在英语和中文分析中都很常见。这种核心叙事是由中国和西方的宣传机构培养出来的,以服务于两地统治阶级的利益。但如此规模的变化几乎永远不能归结为政治领导人的决定,因为这些决定本身就是在回应超越宫廷阴谋层次的问题。镇压的上升不能归结为习近平的独裁个性。
事后看来,“公民社会”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特定时期的特殊产物,在这个时期,经济开放需要并受益于相对的政治开放,国家认为为权利团体支援农民工而背书是有益的,可以填补政府提供福利和法律服务时的空白。此外,人们认为通过中华全国总工会协调的集体谈判和平地提高工人的工资,而不是通过无序的工人罢工不顾一切地提高工资,这为促进国内消费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这种经济背景对于理解这些决定背后的逻辑至关重要。21世纪初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短短十年,记录了最快的经济增长率之一,而危机后的初步放缓又被刺激措施所缓和。但是,随着增长率继续下滑,刺激措施的收益减少,国家对劳工权利保护的支持被撤回,压制也随之增加。这也不仅仅是针对劳工活动的镇压增加的问题。随着统治的经济基础开始动摇,中国国家开始专注于在一系列社会领域重新确立对异议的控制。
虽然对劳工活动者的镇压通常没有针对某些其他群体(如人权律师)的那么严重,但它降低了拘留的门槛,并扩大了涵盖了更多类型的劳工活动者和左派,现在支持工人组织的学生以及社交媒体记者也包括在内了。长期监禁和提出刑事指控并不是主要手段。 相反,大多数人只是被“拘留”了很长一段时间,在此期间,他们基本上无法与家人、律师或外界联系。有些人因刑事指控而被关押,但几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没有审判。还有一些人最终被转移到一个未知的地方并长时间逗留,这种臭名昭著的方法被称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RSDL)。这种慢热的镇压方式避免了严厉公开判决难以避免的场面和愤怒,并通过将过程拖延数月而没有任何新动态,耗尽任何声援活动和媒体兴趣,同时达到相同的目的。其结果是普遍的恐惧和绝望。
进一步加剧悲观情绪的是,中国大陆内部普遍缺乏声援。过去当这种逮捕发生时,其他活动者、左派或学术团体会立即涌现,表达愤怒,签署声明,公开谴责这种骚扰行为,呼吁释放活动者。但自2018年以来的几年里,几乎没有看到这种情况。经过几年的持续攻击,劳工活动者网络受到了极大的恐吓,以至于他们无法再团结在被拘留的活动者周围,因为自己要担心警察上门甚至是拘留。同时,对那些被释放的人持续监视和骚扰,目的是使他们失去作为活动者的能力。曾经充满希望的劳工活动者的场景今天几乎已经面目全非。在这方面,中国政府已经成功地提高了身为倡导者的风险成本,即使是在法律范围内。随着中国大陆支援的日益削弱,除了香港这个更传统的基地外,团结声援的中心转移到了更遥远的国际网络。在2019年香港的抗议运动之后,香港政府一连串迫害和入罪活动者的措施现在也影响到了那些只关注或主要关注中国大陆社会问题的组织,包括几个设在香港的劳工NGO以及香港职工盟(HKCTU)——后者在2021年被迫解散。以香港为基地的活动人士已经很难像过去20年那样组织对大陆同行的声援,这削弱了长期以来对大陆活动人士最有力的外部支持的阵地。
公民社会这所大厦在短短几年内轰然倒塌,也残酷地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这些团体从根本上没有发展出任何强大的社会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他们就没有力量抵御国家的镇压。许多劳工活动者无疑一直在努力建立他们的社会基础,但结果是不平衡的,而且总的来说,受到自我约束和国家镇压的限制。尽管多年来努力建立工人网络,这些团体最终被证明无法在他们试图建立的工人阶级社区中扎根和深入。在一端,以北京为中心的激进学生与工人阶级各个方面的联系比较少,与广州和深圳的学生形成鲜明对比。为了弥补这一点,一些人选择了“融工”作为策略,在工厂工作,目的是组织工人。但这种意识形态干预有走在工人料想的目标前头的风险。它倾向于用学生的意识形态热情代替工人的积极性,最终使活动者隔绝于工友,也隔绝于大学以外任何潜在的支持基础。其他的活动者,如左倾自由主义的公民社会活动者,以及具有农民工背景的更老练的草根活动者,大多在广东作为劳工NGO和准NGO运作。这些活动者在地理上和有机程度上更嵌入工人阶级之中。但大多数人受限于他们NGO的服务模式,更注重帮助工人,而不是赋予他们组织的力量。一个熟悉的悖论出现了,根基最深、参与工人最多的组织也是政治性最弱的,而意识形态意识最强的团体,如 “融工”的学生,在工人中建立有效的根基方面几乎完全失败。最终,最成功的案例是广东的NGO能够发展工人的网络,但从来达不到群众组织那样。少数已经或至少开始走向组织化模式的组织,在开始对工人的斗争产生一定影响后不久就被关闭了。这意味着,面对国家的镇压,工人无法被大量动员起来,支持面临国家攻击的劳工活动者。
时间性很重要。后社会主义时期[19] 的农民工斗争是在1990年代才出现的,与以前的劳工传统没有什么联系,而且持续了不到三十年。相比之下,即使是在农民工行动的高峰期,1990年代和21世纪初,国有企业工人对私有化和工厂关闭的抵抗,也更像一场“工人运动”。这是因为国有企业的工人通过几十年的工业化和社会化,建立了组织能力和受某种国家意识形态支持的群体认同,这个过程至少从1950年代开始——在某些情况下延伸至1949年之前——具有以东北地区为中心的强烈的地区特征。而农民工斗争周期的高峰不那么显著,然后很快地下降,这不仅仅是国家镇压的结果,也反映了无产阶级化和融入新工业部门(特别是私营出口加工部门)的时间较短,在人数开始增长后的二十年内就达到了自己的地区就业高峰–,然后随着去工业化而下降。这和其他很多国家出现的模式相仿,对无产阶级的斗争产生了类似的影响[20]。由于我们在此讨论的劳工行动形式是在沿海出口加工区的移民斗争的背景下出现的,因此,当这种行动形式失去自己的物质基础后,无法在国家的压制下生存下来,也就不足为奇。
当我们见证了中国工人斗争周期的结束,我们就会发现,工人斗争从来没有在组织上或政治上巩固自己,因此,当罢工的浪潮似乎逐渐消失时,就没有什么可以依附的了。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眼前的前景是暗淡的。多年来发展起来的组织和网络本身需要多年的时间来重建。但最重要的是,这样做的政治空间根本不复存在,对学术界越来越多的意识形态控制正是为了将未来的活动者连根拔起。我们面临着失去两代致力于改善社会的中国活动者的可能性。一些最优秀的人被拘留了,其他的人被严密监视,即使是非常小的行动也会被骚扰,甚至是反复拘留。对于那些在工人中成功培养出有机领导力的少数活动者团体来说,情况尤其如此。那些留在中国并没有放弃的人不得不考虑越来越困难、牵涉巨大的个人风险的选择。
上一轮工人斗争中的一些假设需要重新思考。产业工人阶级在本世纪初崛起的想法也被动摇了。即使在国家逐渐去工业化的过程中,产业工人仍然占中国无产阶级的很大一部分,他们的集体力量不应该被低估。就在我们变悲观时,我们一次次对新一波工厂工人的罢工突然爆发感到惊讶。但在就业结构变化和服务行业崛起的背景下,工业斗争已被越来越多地推到后方。这也反映在学术研究中,他们顺应潮流,对服务人员、产业升级和平台经济进行研究。然而,这不仅是焦点的变化,也是一个更根本的视角转换,不再通过工业斗争的视角来看待劳工。
工人斗争的新周期?
2020年代可能成为中国国家不再能够管理资本主义矛盾的十年,这些矛盾在国内表现为住房危机、政府债务上升或工业产能过剩加剧,在国际上表现为与美国的贸易和地缘政治冲突。在经济上升期,工人斗争仅限于获得更大的利润份额,并没有采取反国家的方向,尽管经常抗议政府没有承担责任。但是,当工人的经济要求被其他冲突加剧时,出现的群众运动可能会将其重点扩大到经济收益之外。然而,如果没有公认的组织和领导,任何群众运动可能采取的形式都是不可预知的。一个时代的结束使我们失去了原有的确定性,但它也迫使我们考虑到一个新时代的出现及其斗争的新视野。
也许,有一点能带来希望:在废墟中,即使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也开始出现了新的活动者层。这里活动者团体和支持它们的基础设施(包括社会团体和校园社团)的破坏,使年轻人失去了学习如何组织的空间。但是,在疫情发生的最初几周,人们短暂地看到了行动的有限复苏。当中国当局对疫情的反应准备不足时,人们大多只能靠自己来保护自己和彼此。混乱的局面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他们出于必要而组织起来,同时也是为了社会团结,相互支持。这时,各种各样的互助行动出现了,有些是完全自发的,有些则是利用现有的活动者和他们的网络[21]。例如,围绕劳工权利暂时恢复了宣传工作,重点是需要防护装备的医疗和环卫工人。也有女权主义活动者围绕家庭暴力问题组织起来,在武汉和中国其他地区封锁的最初几个月里,家庭暴力问题激增,还有LGBTQ活动者围绕LGBTQ人群的需求动员起来。公民记者们相信当局没有说实话,于是自己来报道所发生的事情。当然,社会活动的复兴并没有持续很久,在2020年中期,随着政府对这些努力的镇压而消退,人们不应该夸大这种活动者复苏的程度和深度。然而,对于新的活动者来说,这是一个关键时期,可以让他们尝到行动的甜头,对于其他人来说,是他们重新巩固信念的机会[22]。
我们是否看到工人斗争的新周期正在出现?有一些因素可能最终构成一个新的周期。一个有点令人惊讶的发展是仍然有局限的白领工人动员,主要集中在科技行业,该行业曾经蓬勃发展,但现在可能正在破产。即使在2019年的镇压中,关于劳工的公共讨论也没有完全沉默。2019年科技公司员工的反 “996 “动员,揭开了中国年轻职业员工对有毒工作文化(从早上9点到晚上9点,每周6天)不满的现实,随后 “内卷 “进入流行词汇,反映出不仅是过劳,而且是对过劳只导致个人停滞的认识[23]。 最近,这演变成一些观察家所说的中国的 “反工作 “运动,即 “摸鱼 “和 “躺平”[24]。然后,几乎在同一时间,我们看到了2020年公众对送货员的兴趣大增。
在去工业化、结构性就业变化和风险资本对平台公司的投资的推动下,服务行业向零工工作的转变已经导致了一些工人的动员。在越来越多的问题和抗议动员中,自发形成了外卖司机的网络。陈国江,一个曾经的外卖工人转而成为工人权利的倡导者,被亲切地称为 “盟主”,作为一个领导者出现,但他背后没有一个组织。盟主非常自信和有策略,与前几代的劳工领袖相似,他促进了互助,通过在线聊天组将工人联系起来,并通过他在中国流行网站上的在线短视频吸引人们的注意。但偶尔,盟主也会动员工人,领导一些协调行动,针对快递平台对工人的虐待行为。这项组织工作使他从2021年2月被拘留到2022年1月[25]。这大致符合最近逮捕劳工活动者的模式,尤其是越来越多的先发制人的镇压性质。在过去,只要活动者不受限制,他们往往会被容忍数年,然后才可能面临刑事指控的拘留。相比之下,在盟主面临这种命运之前,他只花了几年时间进行低强度的组织活动,按照2000-2010年代的模式,其方式甚至不能被立即识别为 “劳工组织”。受送货工人的条件和集体行动的吸引,一些目前仍然活跃的年轻活动者和学生激进分子对这个行业产生了兴趣,但任何有意义的参与空间仍旧受限[26]。
展望下一轮工人斗争,如果出现的话,似乎上一轮的两代劳工活动者的大多数成员可能根本无法继续他们的工作,无论是由于放弃还是被迫。我们需要关注从事蓝领、白领和粉领工作的新一代年轻工人,他们正试图表达自己的阶级经历,其中一些人正在学习在工作场所内外组织起来。(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如送货员,他们的主要工作场所是街道,而对其他人来说,如在疫情//下远程工作的办公室工作人员,是家庭和网络空间)。他们在公民社会组织和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方面的不足,也意味着他们摆脱了某些意识形态上的负担,被迫尝试新的组织方法,也许可以更自由地阐述他们自己在未来时代的政治。
注释
[1] 关于中国和其他地方的“劳工圈活动”(或者说“援工活动”,英文labor activism)的讨论经常会犯两个错误,而本文则避免了这一错误:他们将工人斗争与劳工圈活动混为一谈,并将21世纪初意义上的劳工圈活动与早期左派干预工人斗争的形式混为一谈。清末民初的工人自我组织形式出现在行会、秘密社团、武术俱乐部、同乡会等。当无政府主义者和后来的共产主义者以及其他人在1910-1920年代开始组织工人时,他们不得不与这些现有的传统合作,建立更接近西方工会模式的组织。(西方模式本身也是从那些不太以劳工问题为中心,而与农民工和早期无产者的生活有更多有机联系的形式中产生的。)1949年后,某些工会被纳入中华全国总工会下的国家机器,而其他类型的工人组织则被取缔。从1950年代中期到1990-2000年代的国有企业改制,当工人试图为自己的利益与国有资本对抗时,他们一般是通过非正式的网络,或者在1960年代末在文革组织的名义下进行。直到1990年代末,一些农民工、劳工律师、社会工作者、左派人士和学者才开始合作成立援工团体,并最终成立非政府组织,成为我们现在所说的“劳工圈”的主要载体。当然,在从中国工业化开始到现在的整个时期,每当工人为自己的利益进行集体斗争时,他们的行动往往是由某些战斗性的同事发起或协调的,他们可能碰巧比其他人有一些更相关的经验。在民国时期,一部分这些战斗性工人会加入与政党有联系的工会,或组建自己的工会。在21世纪初,由于各种历史条件(不限于政治压迫,这在早期和其他有独立工会的地方也存在),这并不是一个选择。这些条件产生了 “劳工圈活动家” 和 “劳工NGO” 的新类别,吸引了一些战斗性工人(假如是民国时代,他们的同行可能会加入工会,或在文革期间加入红卫兵),以及来自其他背景的活动家。这些活动家网络从未发展到像那些早期组织那样的数量或影响力,但它们成为支持农民工的主要模式,直到2010年代末条件再次发生变化。
[2] 譬如见:China on Strike: Narratives of Workers’ Resistance, edited by Hao Ren (Haymarket 2016), 以及 Striking to Survive: Workers’ Resistance to Factory Relocations in China, by Fan Shigang (Haymarket 2018)。中文原文见《珠三角抗争工人口述集》等工厂龙门阵的作品。
[3] 见《林小草的觉醒 2010年南海本田罢工的个人叙述》(包括译者对罢工经常被误解的意义的序言),载《闯》第2期(2019)。
[4] 就在前一年,《时代》杂志选择 “中国工人 “作为其年度人物之一。
[5] 不仅工人运动在历史上有其特殊性,今天中国和其他地方的许多左派将其作为典范,也从根本上误解了这场运动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参见《尾注》第4期的《分离的历史 》和迈克-戴维斯的《旧神新谜》。
[6] 当时,《闯》可能是唯一一个认为在结构上不可能在中国或其他地方出现任何近似古典工人运动的团体,因为全球去工业化的世俗趋势在1990年代已经开始上演(包括其他历史变化),即使是繁荣的中国工业就业也在2012年左右进入最后的衰退。当《前无进途,后无退路》在2015年提出这一论点,充实了《尾注》在《贫苦与债务——论过剩人口与过剩资本的逻辑与历史》(2010年)中已经提出的内容时,它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但当《寻衅滋事》在2019年(《闯》第二期)为同一论点的更新阐述增加经验砝码时,这一趋势及其对无产阶级斗争性质的影响,以及它对以古典工人运动为模式的劳工组织的限制,已经变得有目共睹了。
[7] 一部完整的中国农民工斗争史和相关的劳工活动史仍然需要被书写。在这里,我只是试图对这些群体和他们的决定性特征进行印象式的概括。
[8] 《闯》博客上的译文和分析,见: “Let the People Themselves Decide Whether We’re Guilty” (June 2018), “Locked Up for Reading Books: Voices from the November 15th Incident” (January 2018), 以及 “The Mastermind: A Third Young Leftist Speaks Out on the November 15th Incident” (January 2018)。
[9] 英文和中文资料集,见:“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Jasic Movement – Suitable tactics of intervention?” (Nao Qingchu, 2020)。具体可以推荐的分析见:“Leninists in a Chinese Factory: Reflections on the Jasic Labour Organising Strategy” (Zhang Yueran, Made in China, 2020)。
[10] 摘自Parry Leung, Labor Activists and the New Working Class in China, 2015, pp.161-2。
[11] 译者注: Parry Leung这本书,labor activist的意思在好像是模糊的,包含这两种角色:一、来自同个工作场所的,没有经过组织工作培训的战斗性工人(即“工人积极分子”,英文更合适的表达方法是militant workers);二、来自外面“劳工圈”团体的专业援工人士(即“劳工活动者”,平时意义上的labor activist)。所以我们翻译成“活动者/积极分子”。我们认为这整个框架存在着一些基础性的错误,比如“自发的”行动基本上都是由一些积极的/战斗性的工人发起的,但不是当时作者等“劳工圈”知识分子想象的那么正式的组织方案,工人参与行动的动机与劳工圈活动者干预的目的不一定是一致的(就算那些活动者中有一部分是来自农民工背景的)。
[12] 相比之下,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大规模的拘留和警察暴力在镇压国企工人的抗议中更为常见。这可能是因为这些抗议活动通常比当时大多数农民工斗争的规模更大,组织更明确。
[13] 见Betraying Big Brother: The Feminist Awakening in China by Leta Hong Fincher (2018);《闯》博客可见:“Free the Women’s Day Five! Statements from Chinese workers & students” (March 2015), “Gender War & Social Stability in Xi’s China: Interview with a Friend of the Women’s Day Five” (March 2015), 以及 “Women’s Day & the Feminist Five a year on” (March 2016)。
[14] 见《2015年12月“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镇压事件述评》(2017,Shannon Lee博客),以及 “The Guangdong Six and the rule of law (of value): Theses on the December 3 crackdown”。
[15] 见《搬厂,罢工》工厂龙门阵2013,英文译本为:Striking to Survive: Workers’ Resistance to Factory Relocations in China by Fan Shigang (Haymarket, 2018)。
[16] “Another shoe strike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Lide, Guangzhou” (Nao blog, 2014) 以及 “Lide shoe workers beaten and arrested during assembly in Guangzhou” (Chuang blog, 2015)。
[17] “Activists investigating Ivanka Trump’s China shoe factory detained or missing” (Guardian, 2017)。
[18] “Beijing Evictions, a Winter’s Tale” (Made in China, 2018); “Adding Insult to Injury: Beijing’s Evictions and the Discourse of ‘Low-End Population’” (Chuang blog 2018)。
[19] 编者按:人们常常忘记,在社会主义时代,农村到城市的移民不仅构成了工业劳动力的重要下层,而且还在1967年等关键时刻上演了可以说影响历史进程的重大斗争。见Chinese Workers: A New History by Jackie Sheehan (Routledge 1998), 以及《通向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道路 1949 年以来社会动荡与对动荡的回应如何推动中国的(革命)变革》, 拉尔夫·拉库斯著 (PM Press 2021)。
[20] 例如,见亚伦·贝纳纳夫(Aaron Benanav)在《后稀缺:自动化与未来工作》(中文译本2022)中对中国1990年代的非工业化、2000年代的再工业化和2010年代的非工业化与全球趋势和马克思的 “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 “的讨论。
[21] 这种勇敢和鼓舞人心的自我组织,在《闯》著《社会传染和其他关于中国微生物阶级战争的材料》(Charles H. Kerr,2021)一书中得到了探讨。
[22] 编者按:在这篇文章为2022年的出版进行修订时,中国各地出现了一系列与“清零”措施有关的斗争,大多数是自发的,但有些涉及到由经验丰富的和新的活动家组织的各种类型的活动。其中一些斗争是由工人在工作场所反对 “闭环 “措施以及工资问题而进行的,在12月 清零措施突然结束后,由于疫情供应工厂的关闭而导致的裁员。这一年的其他无产阶级斗争发生在再生产领域,与清零措施对通勤、教育、获得住房、食品和药品的影响作斗争,等等。据我们所知,所有这些基本上都是自发的,但也有可能一些参与者通过参与发展了一些技能和想法,并将其带到未来的动员中。我们希望在今后的文章中更全面地研究2022年的斗争周期,可看我们的博文:“Struggling to Survive in Shanghai and Beyond”; “White Terror, Attacks on Women, Bank Protests, Falling Wages”; “Three Autumn Revolts”; and “Beyond the White Paper: An Interview on the Social Elite in Shanghai’s Protests of November 2022”。
[23] 关于996和内卷的讨论,见 “Involution: Wildcat on China’s 2020” (Chuang blog, 2021)。
[24] 譬如见 “Lying Flat: Profiling the Tangping Attitude” (Made in China, January 2023), “Disarticulating Qingnian” (Made in China, March 2022), “The Tangpingist Manifesto” (Agora, 2021), 以及 ‘Why Chinese youngsters are embracing a philosophy of “slacking-off”’ (Quartz, 2020)。
[25] 关于孟柱的组织活动和被捕,见 “Leader of Delivery Riders Alliance Detained, Solidarity Movement Repressed” (Labor Notes, April 2021) 以及 “Free Mengzhu! An interview with Free Chen Guojiang” (Asia Art Tours, May 2021)。与2018年以来被拘留的许多活动人士一样,孟柱获释后几乎没有任何消息(据我们所知,只是在他的微信频道上有一段模糊的视频)–可能是由于禁言令。
[26] 2020年,流行杂志《人物》上发表了一篇关于送货员条件的深入报道,激发了人们的兴趣。翻译以及关于当年一些外卖员斗争的介绍,请见:“Delivery Workers, Trapped in the System” (Chuang blog, 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