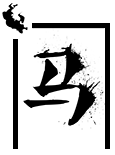Chinese translation of our interview with Lorenzo Fe from GlobalProject.info: “Overcoming mythologies: An interview on the Chuang project” (February 2016). Thanks to our anonymous comrades who translated this.
—
来自GlobalProject.info 的Lorenzo Fe就《闯》杂志第一期(2016年)问了一些问题。以下是我们的回答。1
LFe:首先,请你们先解释一下为什么要启动《闯》计划(project)呢?这个计划到底是关于什么的?你们如何理解目前发生在中国的社会过程的全球性意义?
闯:《闯》团队的一部分发起人从2000年代初就一直在做关于中国的独立研究、翻译、写作和活动组织的工作。这些人原来参与的团队因为政治立场的分歧以及部分成员追求学术道路等原因而解散。后来我们通过更广的反资本主义圈子慢慢结识了一些对中国感兴趣的新同志。2013年,我们聚到一起,讨论了中国的社会变化趋势以及大家要一起做的一些项目。那次聚会中的几个人在其他网站上开了一个英文博客,还有另一些人开始在中文左翼平台上写文章,等等。为了在关于中国的英语讨论中建立起更鲜明和连贯的存在,一部分人最终决定创立自己的网站(Chuangcn.org)并开始筹备杂志。
花额外的精力编辑杂志的念头来源于我们自身的经验:如果是印刷出来的文本,人们会更愿意坐下来读里面有深度的长文章,并且,如果内容和形式都经过精心准备加以呈现的话,人们在一开始就会更感兴趣并把它当回事儿。这些经验主要来自于Endnotes、Sic、 Kosmoprolet 等欧美独立共产主义杂志——我们知道的大部分人都是通过印刷版读了这些文章。当然,我们(和上面这些杂志的编辑一样)也希望我们的作品越普及越好,所以我们也会把内容发布在网上。
至于我们研究和分析中国社会过程的方法及其全球意义,在即将要发行的第一期杂志上的前言里做出了总结:
《闯》由一群共产主义者组成,我们认为“中国问题”与世界经济系统中的矛盾具有重要关联,同时拥有超越该系统的潜能。【……】作为全球化生产链条的关键,中国的危机比任何其他地方的危机都更能威胁资本主义的体制。中国经济的崩溃将标志着一个真正的系统性危机——超越资本主义制度很可能会再一次出现在群众斗争的视野中。
我们的目标是成立一套有着明确导向,能够有助于理解当代中国及其潜在发展轨迹的理论。在第一期杂志中,概括了我们的基本理论框架并对中国目前的阶级矛盾状况进行了说明。我们的杂志中也包含一些中国打工口述的翻译和对参与过这些斗争的无产者的访谈,通过从阶级动态中汲取的一手材料来与我们的理论进行对照,否则后者将会停留在抽象层面。
我们回顾历史既不是为了重蹈左派内部两败俱伤的覆辙,也不想进入历史重演的游戏中,在其中根据一些早就过时了的坐标勾勒出政治路线。而是,我们希望对中国经济历史的回顾可以提供给我们理解这个地区现今冲突的洞见,既明晰“社会主义发展型政体”(socialist developmental regime)的遗产,又了解在这个宣称坚决走共产主义道路的政党控制之下的、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及第二大资本主义经济体中,对所生发出的任何解放事业的独特限制。
LFe:【在你们的文章《进退维谷——全球骚乱时代中的中国》2 中,】尽管你们说,从事生产活动的工人比例在下降,但是似乎在中国被纳入雇佣关系(不管是生产性还是非生产性的雇佣关系)的人口比例还是在上升。中国劳动后备军的相对萎缩很好地说明了过去十几年来中国经历的令人印象深刻的罢工和工资的上涨。这个现象与你们宣称的“对工资的诉求及相关形式的斗争与骚乱相比只是次要的”的观点是不是矛盾的?是不是协调良好的劳工运动的缺失,用国家镇压以及由国家控制的工会合法地垄断对工人的代表,而非“要求涨工资的诉求失去合理性”(illegitimacy of the wage demand)更容易解释——因为这种工资的要求确实存在?以及,如果国家的高度镇压也可以用进一步工资让步的空间之小(由于低利润)来解释的话,是不是也进一步证明工资要求是至关重要的?
闯:首先,我们有必要把上述的问题分解成几部分来进行回答。尽管生产活动(特别是制造业)的雇佣工人比例在下降,越来越多的人被迫依靠工资生活,但是这个和劳动储备大军的萎缩是不一样的。因为历史上的“农民”不是储备军,尽管他们最终无产阶级化了——储备大军是指存在这样的一群人,他们只能依靠工资存活,却因为无法获得工作机会而导致那些在工作的人工资水平下降,因为有一群有工作能力的失业大军,他们需要工作来维持自己的生存。历史上的农民,即使是社会主义时代的形式,也并不只依赖于工资,因而也没有产生上述所说的降低工资的压力,直到出现某些手段切断了人们获取温饱的其他途径。我们第一期杂志中有一篇文章向读者说明了这一过程在中国是如何发生以及如何改变“农民”本质,并且最终使农民无产阶级化的。这一个过程“解放”了以前依赖土地生存非工资收入人口(或者其他非工资生存形式)并且把他们引入工资经济体系。不过,这一过程发生后,我们却没有看到中国总体上的储备大军的“萎缩”。这一现象在2000年代早中期或许是真的,但是到今天已经不是这样了。甚至,现在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越来越少的行业有能力雇佣如此大量的新无产者。传统的生产过剩领域,比如钢铁、煤矿、建筑等行业已经感受到了这样的束缚,未来几年很有可能会进行大量解雇。很多其他工厂在2008-2009年就已经倒闭,还有很多地方,例如东莞,还没有从08年的经济危机中复苏。今天的劳动储备大军是作为普遍的剩余人口增长的一部分在增长——其中,劳动储备大军只是一小部分。
考虑到这一点,就不能确定你是否能将劳动储备大军的某些萎缩与工资的上涨联系到一起,因为劳动储备大军并没有萎缩。确实,现在有劳动短缺的情况,但是这个和基本人口趋势、某些行业的生产力提升、以及农村的资本主义转型密切相关。这一现象也和有些地区还没有从2008年的工厂倒闭以及随之而来的资本和外来工的外流中复苏有关。这是一个“农村劳动力供应过剩下的(城市)外来工短缺”的悖论3。
其次,我们其实并没有宣称罢工和工资要求与骚乱相比是次要的。事实上,这两者经常是结合在一起的。我们只是指出骚乱看上去更普遍,以及骚乱往往卷入更广泛的群众,与旨在通过特定类型的谈判来解决工资问题的非常具体的斗争所不同。但即使是这些基于需求的罢工也并没有传统工人运动的特点,因为许多民工甚至不指望未来在这些地方工作很长时间。工人没有什么动力建立一套可以在工厂中进行根本性的结构重组的机制,或者计划去接管生产干革命,因为工作和个体生命之间没有明确的身份认同——这个和20世纪中期大家可能期待会在底特律的汽车工厂里看到的“终生制”工作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在中国,这些需求通常会以一种类似乘机打劫的形式发生,是一种拿走任何你能拿到的东西的心理。当一个工人可以利用的机会出现时,也许从中他们可以争取回工资、节假日福利、拖欠的福利,或者只是为了报复曾性骚扰工人的经理或曾雇打手殴打工人的雇主,等等;工人们借着这些机会奋起反抗,不过到最后通常都是拿着钱走人。这些行动在变得更加集体化,但是这些行为往往比人们通常预想不同,反而与其他国家的当代罢工和骚乱有更多的相似性。
第三,“要求涨工资的诉求失去合理性”并不意味着工资要求不存在或者不普遍。这个术语是我们从一个法国团队《共产主义理论》(Théorie Communiste)借鉴的,这固然不是最好的表述(他们很喜欢晦涩难解的修辞)。事实上,工资要求的“不合理性”指的是,在全球层面,盈利能力非常有限,资本无法负担全球最低工资水平的提高。这是一个过于简单化的表述,它还有很多其他的后果(通货膨胀、货币动荡、主权债务危机等),但是它在中国发生的形式是,工资本身变成了矛盾的中心点,工资的增长导致了工厂往内地或海外迁移以及自动化加剧。我们在珠三角地区看到各种类似的事情发生,工作场所的罢工更常见的都是争取一次性的支付或福利,并且都是一些不期望继续在工厂里工作抑或认为工厂会搬迁的工人发起的。最近的许多罢工都是旨在从准备搬迁的工厂争取支付欠薪。工人发起的这些罢工,因为这是他们试图获得这些现金的最后机会,而且几乎没有风险,因为他们反正要失去工作。
所以工资要求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只是和历史上欧美工人运动的方式不一样。最主要的差别是,今天的工资要求不能导致一个为蓝领提供高薪产业部门的发展,哪怕通过几十年的斗争。任何带着这种意图或有类似假定的组织,都在犯一个策略性的错误。这些全球性的条件基本上摧毁了历史上营造工人运动发展的环境,所以,那个运动的各种策略也不大可能在当今社会产生作用——哪怕是那些主张要创造高薪就业机会的社会民主“新政”的当代变种、或埃尔福特纲领、或无政府工团主义总罢工、还是由百万计的农民武装领导的革命。所有这些策略的基础都是大规模生产性企业中不断拓展的就业机会,以及从广阔的非资本主义边陲涌入的、由农民转化为工人。这些条件形成社会民主的再分配运动、群众性政党、广泛的工团组织和传统革命军的基础。未来的组织形式将会有很强的组成部分绝对会涉及工作及工作场所,这是必然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传统 “劳工运动”,或任何类似它的运动的崛起。在中国没有这样的运动出现,这并不仅仅归结于打压,因为在欧洲、美国或其他没有像中国这样采取“强硬”打压政策的地方都没有出现这样的运动。中国根本没有这样的“劳工运动”,而正如我们所说:对于共产主义运动实现的可能性来说,这是一件好事。
当然,确实存在大量的积极工人组织和NGO,他们经常在国家镇压中首当其冲——像我们看到的12·3打压。尽管这些组织做了非常重要的工作,然而,他们的规模非常小,并且在一定意义上都没法和历史上20世纪初期中国和其他地方的工人运动相比较。尽管他们有些人会用“工人运动”这个词来描述自己,但是在形式上,他们更类似于当下其他国家社运圈子(activist)的工人互助网络。
LFe:在中国的环境抗争如何与骚乱和罢工有交集?
闯:骚乱常常在警察企图镇压环境保护者时爆发。几乎每个星期都会有类似的中文新闻报道,重大事件也会每隔几个月在英文媒体中出现。
关于环境抗争与罢工的交集,我们还没有听说过那种在工作场所之外出现的对峙事件。这可能反映了一个事实,大多数罢工是由不打算在他们工作的区域安家的外来工发起的。如果把“环境”的定义扩展到工作场所和宿舍恶劣环境的范围,有时就会成为罢工的原因(主要还是针对其他诉求),更多时候,抗议是为了在这些恶劣环境已经导致工人生病或死亡以后,得到治疗或赔偿。
至于超越个体工作场所的环境抗争,与劳动行动结合的主要形式是一个区域的常住居民因为污染而关闭一个工作场所,然后失业的工人通过抗议要求遣散费。这在(2016年)1月底至少发生过两次,在湖南的一家铝厂和安徽的一家钢铁厂。这家铝厂在周围农民的抗议后被关停,因为他们认为这家厂污染水源,导致农业产量减产同时导致疾病如癌症的增加。600多名工人被迫无薪休假,其中400人上街游行示威,徒步7公里要求经济补偿金、拖欠的工资、保险金及医疗检查。医疗检查的要求是出于对环境污染对工人自身健康影响的担心——与农民对环境要求唯一的共同点——但是很显然,他们没有在这一点上做任何与农民团结起来的尝试。一般情况下,这种形式的抗争会把环境抗争者和面临失业的工人置于对立的位置,而且我们还不知道在哪里有出现任何克服这种利益冲突的抗争案例。
LFe: 西方的社会运动支持中国目前发生的斗争最有效的方式是什么?
闯:在高收入国家的社运圈子中,往往有这样的趋势,他们通过以下行动来表明他们对低收入国家的斗争的支持,如在领事馆外游行,或在除了一小撮自我感觉良好的人之外,没有人注意到的小公园表示支持。这些表演的主要作用只是让这些社运人士觉得他们有在“做事情”,并帮助他们在自己的亚文化圈子里提高声望。这部分是由客观的局限性决定的:例如,当一群工人在中国罢工,直到罢工结束,欧美也只有很少人知道,即使它仍然在继续,后者也没有办法在不给工人带来风险的情况下为罢工资金捐款。卷入此类斗争的公司的跨国性质为跨国无产阶级网络提供了给公司施压的机会,但除了以下两种无效的形式之外,我们还没有见过这样的网络。一方面有如SACOM(学生学者监察无良企业行动)这样的消费者导向的网络, 他们旨在给企业施压让他们签署企业社会责任协议。另一方面有小型的独立抵制,例如2014年裕元鞋厂罢工时的一些行动。前者我们可以直接批评他们甚至对最短期的改良主义目标都是无效的,也不利于中国工人组织的发展。后者至少把中国工人的行动作为他们的出发点,试图引起国际无产阶级的支持,但其限制在零售店(主要是无效)的抵制,这阻止了该事件发展成超越小象征性行动的可能。如果这类行动沿着全球供应链的咽喉要道——从制造商蔓延到零售行业——就会更有效。这需要目前缺乏互相交流的物流工人之间建立沟通,不过这在例如欧洲几个国家的仓库工人中已经有一些可喜发展。
在假想中,资本普遍上的和某些特别的公司的全球化特征已经为跨国性的具体行动创造了客观条件,这些可能会严重破坏这些公司的利润空间,从而支持生产工人的颠覆性举措。甚至,这在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真实,主要的限制似乎是不同国家的工人之间缺乏意识和具体的联系——甚至是在同一个国家的同一间公司的工作场所中都是这样。中国处于新的安保机制(技术和政治)的前沿位置,这些机制旨在阻挠中国融入全球市场过程中所激发的跨国无产阶级团结。同时,如果没有在某种方式上联结起跨越国家边界的无产者,这种融入就无法运转,并且,有一些中国工人在利用互联网方面已经变得非常擅长,其中一些行动者在搜罗和传播在其他国家的斗争的资讯,并利用他们的国际联系来支持国内斗争。
《闯》主要是向英语读者传播中国的消息,包括中国无产阶级叙事的翻译和中国社会运动家以及我们自己的分析。我们中的一些人还与现有的中国平台合作,介绍有关其他地方的斗争情况。对于中国以外的无产阶级,我们要强调的是,在21世纪,每个人都在某种程度上与中国有联系。特别是关于共产主义革命的前景,由于中国和中国工人在全球经济中的核心作用,中国无产阶级主义者将毋庸置疑会成为中心,更不用说中国人口的庞大规模。这意味着,如果我们想在任何旨在取代资本主义的运动中发挥作用,我们必须与中国工人发展个人关系,提高我们对中国状况和历史的理解,超越无论是朋友还是敌人灌输给我们的神话。
《闯》计划的目的之一是想帮助在其他国家的人们克服这个神话,并认识到他们作为无产者所经历的情况与中国人所经历的并没有那么不一样。我们知道,目前,这种事情的观众可能只限于某些细分市场——我们在这一点上不抱幻想。但也很明显的是,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放缓,这些问题将越来越频繁地被越来越多的人所问。与许多人在2008年的经济危机之后开始更公开地质疑资本主义的本质相类似,我们认为“中国问题”也开始表现出类似的特征。所以,我们讲的一部分内容至少有可能透过封闭的社运圈子传到其他老百姓的耳中。
备注
- 英文原文:“Overcoming mythologies: An interview on the Chuang project”(2016年2月); 意大利文:“Conflitti sociali in Cina: Intervista al collettivo di ricerca Chuang”;法文:“Surmonter les mythologies: Une interview sur le projet Chuang”;希腊文:“Ξεπερνώντας τους Μύθους: Συνέντευξη με το Chuang project”;捷克文:“Překonat mytologie: Rozhovor o projektu Chuang”。
- 原文:“No Way Forward, No Way Back: China in the Era of Riots”。
- This is the title of a paper on the topic, published in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Vol 51, Issue 4, 2010, by Kam Wing Ch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