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闯》杂志第二期《边疆》(2019年)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第二部分《红尘——中国的资本主义过渡》,此章节原文为《Tiananmen Square & the March into the Institutions》。我们将在未来几周发布《红尘》的中译本全文。
到1980年代中,有少量但数量不断增加的城市人已经打破了单位的铁饭碗。没有了担保就业和国家的粮食配额,他们跳进了扩张中的城市消费者市场所创造出来的新机会。国家鼓励小型企业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比如说,全北京就开满了商铺,售卖通常由乡镇企业部门和/或新的农民工生产的廉价商品,比如温州来的工人,他们在北京的浙江村一个家庭小企业生产时兴的皮外衣。在北京西北片大学集聚的海淀区,清晨出现一长队坐着驴车的农民,正载着货物到集市出卖。街道小贩同样如过江之鲫,使北京的夜生活无比活跃。家家户户开始在单位小楼房和巷道之间的墙上打洞,私人运营餐馆。消费者穿过墙上的洞后进入餐馆,这些馆子提供的食品紧贴城市口味,和服务差劲的国营餐馆那平淡味道形成强烈的对比。
正是在这个节点上可以清晰看到,市场化正在转变那些构成社会主义时代城市的基本空间。各个市场在闹腾,新移民前来定居,自给自足的单位名副其实破墙开放了,这些似乎都象征了自由流动的新时代。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使人回想东亚大陆传统的城市发展模式,比如从唐朝的坊市制转为宋朝的开放城市。这些城市一直被视作介乎闭合和开放的紧张关系之间。与此同时,城市空间开始映照方兴未艾的权力和不平等的新结构。从单位系统逃出来的缓慢涟漪创造出新兴的城市企业家阶级(个体户),人们可以看到他们开着摩托车,甚至开着私家汽车在城里四处奔走。与此同时,农民更经常进入城市空间了,他们既是小规模的自产小贩,也是农民工。这就打破了社会主义时代一直存在的根本性空间分割之一,户口系统也开始了转变,以前是将城市和乡村切割开的方法,现在是对新的无产阶级强力执行劳动规训的分门别类法。农民在城市所居住的空间表明了他们不是以平等的条件进入城市的,街道小贩车子的非正式性质和农民工居住地破烂失修就是明证。城市人开始恐惧城市贫民窟增长的可能,这在官方文件中体现为“拉美化”的风险。
对依然依赖单位系统的绝大部分城市工人来说,生活标准只有缓慢的改善。与此同时,各方面的改变导致阶级构成和联盟的转变,动摇了城市的政治图景。关于腐败的流言和埋怨四处浮现。外国车在街上出现,在坐公交车或者骑自行车慢慢上班的城市人身边路过,这成为人们特别不满的一个对象,此外还有迅速散播的流言,说领导开着梅赛德斯在城里到处走。一开始由于国家压制和生活标准改善,不满情绪大部分还能控制住。但是随着价格改革和高通胀(尤其是食品)从1980年代中开始侵蚀收入,国家要防止对党的批评变成公开抗议变得越来越难。1985和1986年通胀开始飙升的时候,学生开始一系列抗议,要求政治改革和打击腐败。1986年12月初,抗议先从安徽省开始,然后扩散到17个大城市,包括北京。只是抗议没能在大学之外获得支持(最大的抗议发生在上海和北京,但是即便在那里也分别只有3万左右的学生参与),很快就被镇压。1 总书记胡耀邦由于被邓小平等其他中共领导人认为对运动太宽厚,在几周后的1987年1月中辞职。
但是,由于旧户口系统在改革之下继续发挥张力,城市人的不满情绪在1989年之春爆发为改革时代最大的抗议,5月运动高峰的时候,北京的参与人数接近200万。这一次,城市工人加入了起初由学生抗议者搭起的舞台,但是这个联盟最多也是临时的。虽然学生和工人这两个群体当中存在多种意见,但是各自的利益大体上还是将他们推向了两个方向。随着政治形势迅速展开,各个个体被卷入了一场谁都没法真正控制的运动。学生,作为在市场经济扩张中冉冉上升的企业家和经理人阶级的代表,所批判的大多只是改革执行的【方式】。工人,他们对改革的内容有更直接的批判。1989年6月运动被镇压以后,学生再也不会和旧社会主义工业的工人联合起来了。受教育的经纪人阶级成为改革的关键受益人,工人则全盘皆输,只能独自时不时抗议一下,直到世纪之交,社会主义时代工人阶级的残余在去工业化的浪潮下终于被扑灭为止。
同一时间国家对大学校园的管控削弱,这为政治争论创造了新空间,即便在1986年抗议后国家添加了意识形态教育内容也是如此。学生开始探究中国动荡的政治历史,特别是文革的深层次原因。他们转向存在主义、自由主义和新威权主义的理念,开始倾向于这样的观点:政治压迫、官僚权力在日常生活中的独断、腐败、党内的宗派主义,这些都要归咎于中国文化本身。新一场五四运动是必要的,并且必须由知识分子领导。2 讽刺的是,新威权主义在学生那里是最受欢迎的一种意识形态。3 这种意识形态的基本理念是,必须由中共内一个单一的强硬领袖来控制党,防止出现宗派之争和妨碍改革进程的官僚不作为。这个领袖应该接受知识分子的意见,因为知识分子理应明白如何改革社会。学生当中也有对威权主义的自由派批评,另外还有更少量的学生,批评改革的方向损害了普通公民的生活水平。不过,这个时期虽然有种种含糊的“自由”和“民主”说法,但是大多学生似乎沉醉在这样的想法:只有他们明白如何解决中国的问题。4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的时候,学生马上开始在校园写大字报并展开讨论。胡耀邦在学生和知识分子那里特别受欢迎,因为改革伊始他就承担了为知识分子平反、重建党与他们的关系等任务。他被看作“不可腐蚀者”,是要保护自身特权的强硬官僚所孤立的党内正确领导的象征。学生当中有些小组,尤其是在党内有着不错人脉的小组,在天安门广场中央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安置花圈来纪念他(1976年周恩来总理逝世后北京市民也这样做了,四五运动由此引发)。第一次学生抗议发生在4月17日,他们从大学校区开始夜间游行到广场,大约有1万人。带头的学生举着标语,宣布他们是“中国魂”——这个精英主义的表态将成为未来两个月他们的政治的特征。广场中心的纪念碑很快放满了纪念胡耀邦的花圈,头几天谁都可以跳上来纪念碑的前几级台阶,向几百个观众发表演讲。晚上,抗议者通常在中共高层领导人生活的中南海大门前聚集。
不过,年轻工人和无业的城市人很快加入了学生和知识分子,其中最重要一步是组建了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5 只是这两个社会群体虽然共同参与了事件,却没有一道形成统一的社会运动。他们临时走在一起,是因为他们都反对被市场改革加剧的党内腐败,但是他们之间的分歧点比团结点还多。至于抗议风格,学生宣布运动只属于他们,因为他们担心无法控制其他团体,因为其他团体可能使用暴力,或者给了国家镇压的借口。他们尝试将其他人排除出抗议,如果不行就排挤其他团体,只能当支持者,不能完全参与。因为学生和知识分子相信他们是唯一可以“救国”的人,所以他们经常责怪“农民”在革命和社会主义时代让国家走了弯路。运动早期,学生为了尝试控制运动,建立了北京高校学生自治会作为协调组织,领导层通过选举产生。4月24日,高自联组织了大范围的大学课程杯葛行动。随着抗议进行,其他学生组织也开始组建起来争夺控制权。独立的北京高校学生对话代表团尝试和党的领导人讨论诉求,但是讨论被其他学生扰乱了。天安门广场的占领行动由保卫天安门广场总指挥部控制,这又是一个独立的学生组织。总指挥部的领导层由占领广场的学生选举产生,所享受的主要权力就是在抗议中心控制一套扬声器系统。除此之外,学生还将纪念碑附近的广场中心空间围出了等级制度一样的同心圆。要走到这些同心圆的外围,你得是学生,如果要再进去圆心,你得是学生领导,和总指挥部有关系。学生强迫工人组织在广场外的街道对面设立自己的营地。
和工人相比,学生与改革的关系也十分不同。学生大部分希望改革提速,希望改革的组织更优,效率更高。他们害怕腐败会导致改革削弱。不过到1980年代中,工人已经开始看到自身的利益被损害。当时出现了新失业(现在要自负盈亏的国企有权辞退工人了),工资停滞,还有更重要的高通胀。到1988年底,通胀达到了超高水平。对工人来说,改革必须放缓或者作出重大反思。物价稳定尤其是关键,因为工人正在丧失国家补贴的低价粮食担保。学生一开始关注的大多是哀悼亲知识分子的胡耀邦,而工人对党及其改革派政策的批评,和运动初期的学生相比更具备广泛的政治性。工人认为,腐败之所以是问题,不是因为会削弱改革,而是因为表明阶级不平等出现了新的形式。工人在传单里问道,邓小平的儿子在香港赛马输了多少钱,赵紫阳打高尔夫有没有掏钱,领导人还有多少套宅子。他们还继续追问,中国在改革进程中拿了多少国际债务。
学生和工人还对民主有非常不同的理解。学生的民主说法很含糊,但通常是呼吁知识分子要和党建立特殊关系。许多学生更感兴趣的是让赵紫阳成为权力更大的开明领袖,这样知识分子就可以充当顾问,展示市场经济究竟该如何运作。如果和工人聊聊,就会发现他们的民主理念更加具体,这个理念早就出现在中国长期的工人斗争当中了,比如说在1956-1957年的罢工、文革和1970年代就非常清晰。6 对许多工人来说,民主确保的是工人在他们工作所在的企业内部的权力。工人抱怨的是工作单位里的“一人独尊”政策,也就是厂长实际上成了“独裁者”。7
学生和工人不同,他们密切参与了中共内部的宗派斗争。学生大部分站在当时的总书记、更极端的市场改革派赵紫阳一边,当时赵紫阳想加速推动改革。另一方面,学生大部分都肆意谩骂国务院总理李鹏,当时距离5月底他成为军事戒严的代表人物还很远。李鹏是温和的改革派,被人们视为旧式官僚,妨碍了通往理性市场经济的迅速又高效的过渡路线。工人实际上没有参与这场宗派斗争。他们之前参与宗派斗争的时候几无获益,尤其是在文革和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的民主墙运动。工自联警告说,“……部分政治野心家,利用这次民主运动,达到个篡权上台的目的。邓小平正是利用了人民的‘四·五’运动而上台后暴露出来的杀机”。8 党员对学生投桃报李:中华全国总工会公开支持学生,却无视参与其中的工人和他们羽翼未丰的组织。9 不过,随着5月局势发展,党内元老逐渐不支持赵紫阳总书记对学生的忍让做法。5月17日在邓小平住所召开了一次激烈的常委会会议,邓小平和李鹏批评赵紫阳的做法,宣称他在分裂党。邓小平促成了宣布戒严,随后5月20日正式施行。5月19日拂晓,赵紫阳到广场警告学生要离开了,说他们不能为了一场已经结束的运动而牺牲自己。这之后已经丧失党内职务的赵紫阳离开了广场,不久就被软禁终生。5月底宣布戒严,激化了参与者的政治,此时工自联宣布“‘人民公仆’们[党]侵吞了人民尽血汗创造的全部剩余价值!”“只有两个阶级,即: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10 相反,大多数学生即便在宣布戒严之后依然苦苦追求赵紫阳一派的支持。在政治环境迅速变化的压力之下,学生和工人之间潜在的联盟永远无法实现了。
学生一开始告诉工人不要罢工,这样运动的重心就能维持在他们身上,重心之内的力量也可以保存。不过5月20日宣布戒严之后,学生终于看到了工人参与的重要性(虽然又只是支援作用),他们终于请求工人进行大罢工。但是到了那个时候,抗议的参与度已经大幅下滑,工人要充分动员自己的队伍为时已晚。只是,工人还是能够拉上大批人抵抗戒严。事实上,学生数量萎缩的时候,工人拉上街的人在继续增多。但是在这个时候,党已经在北京外围汇集了至多25万军队。工人和其他的城市居民在一开始的6月2日晚至3日,还能封锁道路,用车辆包围部队,从而阻止军队入城。这只引发了少量的暴力冲突,城市居民通常给困在人群中的疲劳士兵提供食物,直至几个小时后士兵放弃,撤出市中心。这只能怂恿接下来一晚上出现更多的抵抗。
但是在6月3日晚至4日,军队更加坚决地朝广场前进,要中止这些抗议。当晚主要是工人和无业青年试图拖延军队在通往广场的大街上的前进,其中有许多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上百平民死亡(其中甚少是学生)。在天安门东西向的主要大道长安街两旁,有工人和其他北京居民用公共汽车构建路障,通常还点火燃烧。军队靠近的时候他们就扔燃烧瓶和石头。广场以西木樨地和长安街交接点的打击尤其严重,工人和士兵之间发生了激烈战斗,大批人丧生于此。第一批装甲输送车的士兵抵达广场的时候,一些学生和居民继续抵抗,有一辆装甲输送车着火燃烧。多名平民在广场周边遇害。军队的主力一到广场就停下,清晨之前与剩下占领广场的学生谈判,允许他们离开广场步行回到校园,不过有一些在离开前先被士兵打了一顿。首都的抗议结束了,但是镇压仍在继续。随后的几天和几周,工人在刑期和处决上遭受最大的打击,而对参与的学生,判决则宽大得多。
严厉打压参与运动的工人,成为了1990年代市场改革加速的条件,最显著的是1990年代初的食品市场自由化,因为工人本来一定会抵抗的。随着1989年之后中国经济愈发融入全球资本主义,学生和工人之间的经济利益也进一步分化了。1980年代的学生成为1990年代的中间和企业家阶层,他们获益于抗议被打压后得以继续的市场改革。11 1990年代末,许多老国有企业的工人被辞退,入城的移民迅速增加,“新工人”阶级形成了,在全球制造业系统内部的他们工资低下,生活条件不稳定。工人和农民的抗议从1990年代中开始重新增加的时候,学生和知识分子没有加入他们,他们就算还有一点政治也大部分右转了,倡议保护产权和言论自由,又或者逐渐采纳民族主义立场。
- Julia Kwong, “The 1986 Student Demonstrations in China: A Democratic Movement?” Asian Survey 28(9), 1988, pp. 970-985.
- 五四运动发生于1919年,由知识分子领导,涉及对中国政治的文化批判。中共在这次运动脱颖而出。
- 关于中国新威权主义的发展历程,见Joseph Fewsmith, China Since Tiananmen: The Politics of Trans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86-93.
- 除非特别说明,否则本部分的信息均出自与运动参与者的谈话记录。
- 本部分关于工人参与运动的信息大部分来自Andrew G. Walder and Gong Xiaoxia, “Workers in the Tiananmen Protests: The Politics of the Beijing Workers’ Autonomous Federation,”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29, January 1, 1993. 其余信息来自与参与者的对话记录。
- Jackie Sheehan, Chinese Workers: A New History, Routledge, 1998.
- Walder and Gong, p. 18.
- “告全国同胞书”,《工人起來了——工人自治聯合會運動1989》,香港工會教育中心,1990,p. 223.
- Walder and Gong, p. 7.
- “告全国同胞书”,《工人起來了——工人自治聯合會運動1989》,p. 223.
- 一个证明就是受到追捧的电影《中国合伙人》,这是对新东方教育公司如何创立的戏剧化表现。电影开始,创立人还是1980年代末的任性大学生,他发扬红卫兵的反威权主义,要质问老师对美国社会的邪恶的成见(“你知道什么?你根本没去过美国!”)。这种亲西方的态度在1990年代与民族主义取向一起悖论般发展,这时候主人公希望其他可以上进的年轻人具有英语语言能力和自信心,在全球市场实现财富和权力的同时,重新塑造自己的民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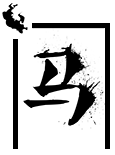

> 学生,他们是市场经济扩张的时候企业家和经理人这个上升中阶级的代表,对改革执行的方式持最批判的态度。
这一句的翻译有误。这里的原文是:
> Students—representing a rising class of entrepreneurs and managers in the expanding market economy—were mostly critical of the *way* that the reforms were being implemented.
引文重点如原文。
应当翻译为:
学生,作为在市场经济扩张中冉冉上升的企业家和经理人阶级的代表,所批判的大多只是改革执行的【方式】。
谢谢!我们采用了您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