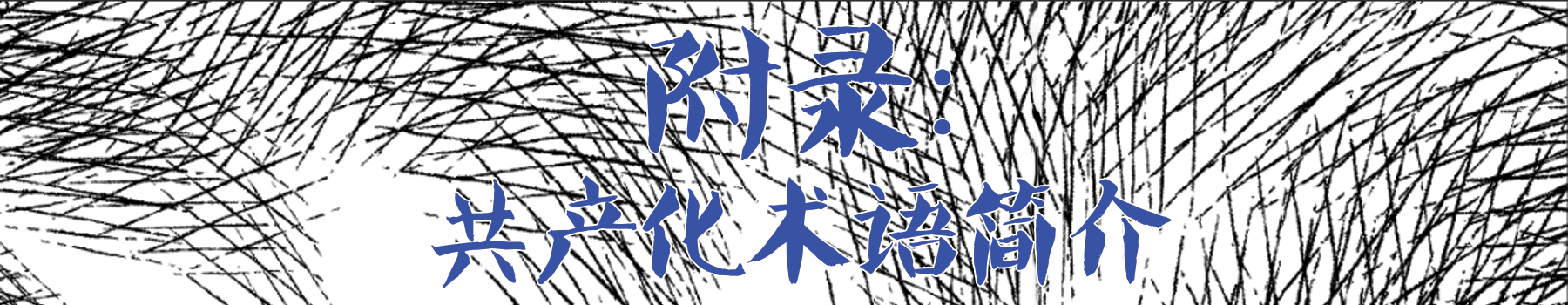
共产化术语简介:目录
“尾注”[1]
endnotes
这一稀奇古怪的名字在刊物第一期中没有直接的解释,但是通过浏览前言《把你的尸体拖出来!》可以感觉出来标题中的end(尾/终结/末日)所暗示的多层含义:
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 十九世纪的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它在破除一切对过去的事物的迷信以前,是不能开始实现自身的任务的。从前的革命需要回忆过去的世界历史事件,为的是向自己隐瞒自己的内容。十九世纪的革命一定要让死者去埋葬他们自己的死者,为的是自己能弄清自己的内容。【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如果说在马克思写这段话时,人们只能用未来时态谈共产主义,那么在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可以谈自己“历史”(且仿佛不谈其他事)的今天,就更是如此了。马克思主义本身已成为逝去几代人的传统,而甚至后世的情境主义者似乎也难以“离开二十世纪”。
我们这样写并不是出于对当代的迷恋,也不是出于要使共产主义理论“与时俱进”的欲望。二十一世纪和上个世纪一样, 是由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矛盾、工作和“生活”之间的分离以及抽象价值形式对一切的支配所形成的。因此,它和前一个世纪一样值得我们离开。然而,情境主义者所了解的二十世纪,其阶级关系的轮廓、进步的时间性以及关于如何能超越资本主义的视野/地平线(post-capitalist horizons),显然都已在身后。如果我们已经厌倦了新奇理论(如后现代主义、后福特主义和学术界的各种新产品),与其说这些理论未能掌握本质上的连续性,不如说1970年代和80年代的资本主义重构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
在本期《尾注》初刊中,我们收集了一系列与二十世纪革命史有关的文章【……】这些革命的历史是一部失败史,要么是因为它们被资本主义反革命所粉碎,要么是因为它们的 “胜利” 本身就采取了反革命的形式——它们所建立的社会制度还依赖货币交换和雇佣劳动,所以未能超越资本主义。不过,后者不能简单化解释为 “背叛”,前者也不能解释为“战略失误”或 “历史条件”缺失的结果。当我们试图分析这些失败的时候,我们不能借助“如果”式的反事实,将革命运动的失败归咎于除了运动本身的决定性内容以外的一切(领袖、组织形式、错误的思想、不成熟的条件)。【……】
我们出版这些“历史”文章,并不是要鼓励对历史本身的兴趣,也不是要恢复对革命史或工人运动史的兴趣。我们希望,在思考上个世纪斗争的内容时,我们将帮助打破这样一种幻想,以为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我们的”过去,是需要保护或保存的东西。【以上引用的】马克思的箴言提醒我们必须摆脱传统的束缚。我们甚至可以说,除了认识到将我们与他们分离的历史断裂之外,我们没有什么可以从过去革命的失败中学习的——没有必要重演失败以发现它们的“错误”或提炼它们的 “真理”——因为无论如何都不可能重复它们。当我们为这段历史“记录得失明细”而认为它已经结束了的时候,我们同时也在画一条强调自己时代斗争的线。[2]
革命视野/地平线、工人运动
revolutionary horizons, the workers’ movement
在《一部分离的历史》等文中,《尾注》将资本主义世界史上的无产阶级斗争及从中出现的共产主义运动分成不同的革命“地平线”(又可译为“视野”,但是“地平线”一词更适合《尾注》想表达的客观方面:关于共产主义如何能实现的在不同时期的不同想象和方案,主要是来自当时的物质条件)。什么叫“地平线”呢?在《尾注》第二期的前言《阶级关系中的危机》[3],作者解释:
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两个阶级之间的】关系的每一极【资本与(被当作劳动力的)无产阶级】都可以自相矛盾地宣称自己是真理,而且由于它是一种动态关系,其核心是资本增殖过程的未来导向性所产生的方向性,因此阶级关系始终承载着一个内在的时间地平线。它不会简单地将自身永恒化为一个庞大、封闭的总体性。相反,作为一种斗争关系,它本身就包含着对未来的想象,作为这种对立的预期解决方案——这就是它的地平线。工人阶级的最终胜利、自由资本主义的确立、迫在眉睫的野蛮主义或生态启示录:阶级斗争总是有一个单一的地平线,而根据阶级关系在任何特定时刻的动态,这个地平线具有不同的性质。在这个地平线之内,将出现多少具备矛盾性的超越方案。如果单凭阶级关系中某一极取得胜利就能超越资本主义阶级关系是不可能的——因为任何一方离开另一方就无法存在——那么,当20世纪革命的内容是将工人阶级肯定为工人阶级时,它们所争取的对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的超越就不可能实现。与此相比,作为共产化【communization】的革命只会出现在某种斗争中:这种斗争在其内在地平线中蕴含着阶级关系的直接“非再生产”。
《尾注》认为,阶级关系所承载的革命地平线在特定时刻的具体特征是根据阶级关系的历史变化而决定的:
这个地平线的变化特征是革命理论的主要基础和对象…… 我们追溯这一地平线的现状……以及它曾经的面貌,将我们面临的地貌与过去的地貌区分开来。共产主义理论就是关于阶级斗争内在地平线的理论。通过追溯这一地平线并分析它的转变,我们使阶级斗争的历史性特点成为理论的确定对象,并在其有限性中加以把握。
按道理来说,资本主义世界史上每个时期或甚至每个地域可能有不同的革命地平线,但是《尾注》主要强调两种:将无产阶级肯定为工人阶级的地平线(就是TC所说的“纲领主义”【programmatism】),以及直接否定整个阶级关系及其中的两极(包括无产阶级本身)的地平线(即“共产化”)。
在《一部分离的历史》,作者主要想解释为什么经典工人运动(《尾注》认为它是于1883年登上历史舞台的,于1982年下台的)虽然最初将其目的设定为整个阶级关系的否定(这在巴黎公社时代的工人口号和马克思等人的作品中都是比较明确的),然而,随着资本积累过程对世界格局的重组,无论是在实践上还是在运动领袖的理论上(从列宁主义到无政府工团主义、社会民主改良主义党派和工会,以及再到第三世界民族解放情况下的工人运动),都越来越达成了新的共识:为了消灭无产阶级状态,先需要将此状态普遍化;为了消灭工作,先需要让更多的人变成工人,而将“劳动”从要摆脱的铁链使之神化为“光荣”;为了消灭阶级社会,先需让工人当统治阶级,来管理与资本主义大同小异的工业社会。这种共识就是法国“共产主义理论”小组(简称TC)所谈的“纲领主义”地平线,而《一部分离的历史》试图解释其背后的物质根源。在此基础上,他们试图解释为什么世界范围内多数地域的工人运动会在1970年代前后分解(包括韩国工人运动于1980年代的分解),而与此同时,纲领主义的地平线为什么会让位于“共产化”的视野?
“工人运动” 与 “有组织的工人斗争”
the workers’ movement vs. organized worker struggles
《尾注》、TC和其他与“共产化思潮”有关的团体经常强调两个容易被误解的问题:“工人运动”不等于“有组织的工人(或无产阶级)斗争”,以及“无产者”不等于“工人”。在这里,“工人运动”一词专指是从19世界末的1980年代的经典工人运动,包括各种机构(工会、党派、杂志出版社、俱乐部、住宿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图书馆、培训中心、托儿所等等)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整个世界观、工人认同和工人文化。虽然在这段历史之前和之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世界各地必然会有工人斗争,有些地方甚至还有强有力的工会等组织,这些现象的物质条件、斗争的具体目的和方式、组织的特点和主导性思想(总之,它们的“地平线”)与经典意义上的工人运动形成着明确的断裂。
“工人” 与 “无产者”
workers vs. proletarians
大部分的无产者不是“工人”,这个通过中文的词汇“无产阶级”比较容易看出来:虽然纲领主义话语经常会把两者混为一谈,但是在马克思等人在19世纪中期开始借用古罗马的这个词(proletarian)的时候,他们想强调的关键特点不是“打工人”(毕竟历史上一直有人打工),而是被迫与生存资料相分离的人。“无产阶级”这个现象不像历史上偶尔因为战争等灾难让个别地域的人群变成难民(直到他们逃到安全的地方之后成立了新的聚落),而是全世界范围内大多数人逐渐加入前所未有的生存困境:对货币经济的彻底依赖,除了找办法挣钱的话,就没有办法生存。不过,从这一阶级在近代英国“圈地运动”被迫登上历史舞台开始,直到无产阶级化在20世纪末成为全球的新常态时,其中能够找到稳定工作的人一直只能算少数,其他人如小孩子、老人、家庭主妇、残疾人士,甚至在适龄健全男性之中,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或多或少总有人找不到稳定的工作,如果家里还有一点地就需要耕田来弥补,没有的话就需要依赖灰色经济、借钱、各种救济金等方式才能生存。基本上只有在工业化上升时期的欧美等地方的特殊情况下才会有越来越多的无产者开始进工厂打工,使大家想象无产者早晚都会变成工人,以及工人(尤其是制造业的技工)可以成为整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就像《尾注》在《一部分离的历史》详细研究的那样。
到了1970年代以后,《尾注》在《贫苦与债务》等文中分析的“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即由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等因素导致的世界规模利润率下降、经济停滞、去工业化、过剩人口的增长等漫长的趋势,逐渐让无产者和工人之间的区别变得比较明显。比如近年的许多无产阶级斗争是围绕着再生产领域的(包括公共社会服务的紧缩、生态问题与气候变化、警察暴力与“种族化”问题、“贱斥”过程与性别问题等),往往与工作场所没有直接关系,连那些有稳定工作的参与者通常也不会强调 “工人”的身份。在当代“阶级分解”(阶级构成成为问题)的情况下,强调工人的身份有时候甚至会在具体的无产阶级抗争中不受欢迎,有固定工作和工会的工人有时候被看成是阶级内部稍微有“特权”的分支。因此,为了开辟新的阶级构成道路,无产者也许需要在21世纪的斗争中寻找与20世纪工人运动及其工人身份之外的方案。(见《盘旋待降》和《前进吧,野蛮人!》。)
共产化
communization
在《共产化与价值形式理论》一文中,《尾注》的作者解释:
共产化理论出现的时候【1970年代】是一种批判,其批判对象是各种继承自第二和第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工人运动的革命认知,以及运动中的异议趋向和反对声音。20世纪上半叶,革命失败的经验似乎端出了一个本质问题:工人能否或者应否通过党和国家(列宁主义,意大利共产左翼【即“博尔迪加主义”】)还是通过生产节点上的组织(无政府工团主义,荷兰/德国共产左翼【即“工委共产主义”】)来行使权力?一方面,有人会宣称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错失革命机会,正是因为党不在场——或者说正确类型的党不在场;而另一方面,其他人会说正是党和革命的、“国家主义”的、“政治”的概念在俄罗斯失败了,并在其他地方发挥消极作用。
共产化理论的发展者【由法国共产左翼于1968年五月风暴之后分裂出来的团体如“共产主义运动”(Mouvement Communiste)、“否定”(Négation)以及“社会战争”(La Guerre Sociale)】抗拒这样以组织形式来安放革命的倾向,转而瞄准通过革命内容来把握革命。共产化拒绝将革命视作工人在获得权力之后经历一个过渡时期的事件:相反,我们应该将革命视作以无中介的共产主义措施为特征的运动(比如免费分配生活必需品),这样做既是措施本身的特征使然,也是摧毁反革命的物质基础的一种方法。革命以后,如果资产阶级财产被没收,但是工人依然是工人,依然在不同企业进行生产,生计依然依赖自己与工作场所的关系,依然与其他企业交换,那么,不论这种交换是工人自我组织还是由“工人国家”给予集中指导,都意义不大:资本主义的内容依然,资本家的独特角色或者功能迟早会重新自我树立。作为共产化运动的革命则截然不同,它将不再构建和再生产所有资本主义范畴,从而摧毁它们:交换、货币、商品、不同企业的存在、国家,还有最根本的雇佣劳动和工人阶级本身。
共产化理论的诞生,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认识到了用另一套组织形式(民主、反威权、工委会)来反对列宁主义的党国模式的做法,还没有达到问题的根源。另一原因在于,这种关于革命的新思考出自当时走到前台的阶级斗争特色与形式(比如毁坏设备、缺勤和其他抗拒工作的形式)以及工作场所之外的社会运动。所有这些都可以看作在拒绝肯定工作,拒绝肯定工人身份是革命的基础。情境主义国际(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的作品是共产化观点发展的一大刺激。秉持着植根于日常生活转型的总体革命的视角,情境主义国际已经感受到并理论化了斗争所表现的新需求,因此人们在之后承认他们最能预示和表现1968年法国事件的精神。
在《尾注》第一期的前言《把你的尸体拖出来》还有一段话可以用来补充上述这个简介:
另一种思潮以“共产主义理论”小组【Théorie Communiste,简称TC】为代表,试图对共产化命题本身进行历史化,将其理解为阶级关系变动的结果,当时【1970年代末至1990年代】这些变动正在逐渐破坏工人运动的制度【如工会和左翼党派】以及整体的工人阶级身份。他们将继续将这一变动分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根本性重构,这对应前个斗争周期的终结,以及新的斗争周期在【1960年代末】反革命成功之后的出现。对于TC来说,新周期的显著特征在于,它的内在具有共产化的潜力,因为新时代阶级矛盾的“极限”现在处于再生产的层面上。[4]
这也就是前周期工人运动所谓“纲领主义”革命地平线的终结和新周期共产化地平线的开始。
纲领主义
programmatism
“纲领主义”是TC(即法国“共产主义理论”刊物小组)的历史分期法的关键概念之一,他们将之定义为:
作为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无产阶级在争取解放的过程中,找到了未来社会组织的基本要素,这些要素成为待实现的纲领。因此,无论是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工人委员会、劳动的解放、过渡时期、国家的消亡、普遍的自我管理,还是“联合生产者社会”,这场革命都是是对无产阶级的肯定。纲领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理论——它首先是无产阶级的实践,在这种实践中,提升的阶级力量(体现在工会和议会中、在组织上、在社会力量的关系上,或者在对“历史教训”的一定程度的认知之上)被积极地视为通向革命和共产主义的垫脚石。纲领主义同无产阶级和资本之间的矛盾有着内在的联系,因为这个矛盾是通过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从属【formal subsumption】而构建的。[5]
根据TC的观点,纲领主义时代大约于 1970 年代结束,在此之前,资本对劳动的实际从属(real subsumption)变得如此彻底,以至于无产阶级不再有任何可以在夺取政权后以实施革命纲领的形式加以肯定的本质。相反,现在的共产主义革命只能被视为无产阶级对其作为一个阶级的存在的集体自我否定。关于共产主义革命的这种新的理解就是TC所说的“共产化”——这一术语在吉尔·多维(Gilles Dauvé)等其他法国极左派理论家(以及后来的《尾注》和与《铁群》(Tiqqun)杂志有关的某些无政府倾向)那里也能看到,但TC使用这一术语的方式有所不同,主要是在把它历史化为新物质条件(1960年代“实际从属”过程完成)的表现。
形式/实际从属
formal/real subsumption
虽然《尾注》对共产主义运动史的分期方法最初是由法国《共产主义理论》杂志小组(简称TC)提出的,至于具体应该如何分期和解释,前者与TC之间有一些分歧,而《一部分离的历史》就是在这种批判的基础上进行研究所产生的结果。
分歧之一在于,《尾注》不同意TC使用马克思“形式/实际从属”这个概念来分期。在马克思那里,“从属” 指资本为了生产剩余价值对劳动的控制。在《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6],马克思将其分为“形式上的从属”和“实际上的从属”,前者指早期的产业资本采取雇佣的形式来剥削使用传统工具的工人,但不改变生产过程,后者指在工业革命阶段,资本开始通过强迫工人使用机器等手段来改变生产过程。然而,TC把这两个概念的范围扩展为整个时代的特点,并且用来解释当时无产阶级“斗争周期”的性质:他们认为,在20世纪初出现的“纲领主义斗争周期”相当于形式从属的完成和实际从属的开始,而在1970年代出现的“共产化斗争周期”相当于实际从属过程的完成。
《尾注》的批判指出,资本对劳动过程的从属从形式阶段发展到实际阶段,在不同产业和国家都有着不同的历史时期,所以无法把这个变化联系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中无产者抗争和共产主义地平线在不同年代的特点。TC这种思维也许能反映他们以法国为中心的历史观:‘这个图式只在法国完美契合(最多应用于西欧),要将之延伸到世界他处困难重重,尤其与落后和后发国家脱节。’《尾注》承认 ‘TC区分形式上和实际上的从属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过两者‘并非对应两个阶段,而是大致对应工人运动展开时所处的世界的两个方面’: “形式从属”的方面涉及工人运动时代的农民群体(peasantry,包括小农和传统的农村统治阶级)‘仍有一部分处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外;这个外界当时处于被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吸纳的过程中,但这个过程用时许久。’ 与此同时,“实际从属”的方面涉及 “生产力的发展”,即 ‘劳动生产率的累进增长和相应的转型,这种转型既包括生产设备,也包括设备所依赖的的资本主义社会基础设施。’ 而 ‘这两个方面相应催生了工人运动的两个迫切任务:一方面要与旧制度精英斗争,他们企图剥夺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之下的工人的自由(比如投票权,选择雇主的权利);另一方面要将生产力的发展从它的桎梏中释放出来,尤其在后发国家(这些桎梏通常出自旧制度的持续存在)’。因此,《尾注》认为共产主义地平线在1970年代发生的断裂不能简单归因为“实际从属的初期阶段”正好在那个时候结束了,而是因为‘劳动过程的持续转型、农民的终结、资本主义积累在全球范围的放缓,以及对应的长时期去工业化的滥觞’。
斗争周期
cycles of struggle
《尾注》在《一部分离的历史》介绍的相对于TC历史观的另一个分歧点涉及“斗争周期”与“革命地平线”的差别:
TC通常将工人运动(“纲领主义”时代)称为一个“斗争周期”,于是他们没能清晰区分两个概念:斗争的周期性浪潮,以及周期展开的时候身处的共产主义地平线。这两个概念对我们的20世纪资产负债表来说皆系必要。
斗争周期的概念描述的是阶级冲突发生的方式。这种冲突一般不在长途跋涉或者短暂爆发中展开,而在浪潮之中展开。有这么一些反动时期,革命势力疲软间歇但不完全缺席,这些时段可能持续几十年,但总会在无比难以提前预测的时刻结束。此后暴动爆发得越来越频繁。以往大家并不在意的斗士会发现,自己的人数日益壮大。与此同时,斗争具备了新内容,演化出新策略,发现了新组织形式(这三者只能通过苦难和报复的可怕肉搏战才能赢得)。假以时日,斗争会各方汇聚——但从来不是线性的汇聚——在多年的时间里潮起潮落。这就是革命成为可能的原因。等到革命失败或者反革命成功的时候,周期就会结束,新的反动时期就会开始。
革命战略家大多数关心的是各个斗争周期的高潮点:1917年、1936年、1949年、1968年、1977年,等等等等。如此一来,他们通常忽略了这些周期展开时所处的背景。工人运动就是这个背景,为不同的周期展开提供了布景,比如说(在欧洲)1905–1921,1934–1947,1968–1977。正是因为每个斗争周期在工人运动的背景之中展开,我们才能分辨出其中的高潮点:这些高潮点不但是资本主义阶级关系内部的崩裂,还是在特定的共产主义地平线内部产生的崩裂。……我们的主张是,只有整体考究工人运动而不是只考究不同的高潮点,我们才能看出这些高潮点何以不同,甚至看出何以与众不同。工人运动时代的革命尽管和总体潮流并不契合,却还是出现了,这完全和当时认为大势所趋的革命理论相悖。
所以我们认为,工人运动本身不是斗争周期。运动指向一种有界限的共产主义地平线,而这种地平线在赋予斗争某种动力的同时,也确立了斗争的局限。要说工人运动是共产主义的一种前景,就等于说运动不是不可更易的前景。认为共产主义只有在工人运动复兴的基础上才能再次成为可能的想法(这种复兴和有组织的工人斗争不是一回事),是有必要摒弃的。我们将在本文尝试理解,19世纪末叶到1970年代期间的状况,是如何开启了工人运动的时代,如何引出了多个斗争周期,又如何无可挽回地崩溃。
阶级分解、构成问题
class decomposition, the composition problem
《尾注》在《贫苦与债务》、《一部分离的历史》、《前进吧,野蛮人!》等文中使用的“无产阶级分解”概念来源于意大利1960年代 “工人主义”(operaismo)中的“阶级构成”(class composition)概念。后者可分为两个方面来解释:
一、无产阶级的‘技术构成’是指资本如何把劳动人口组织起来并加以利用,即工人在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具体条件(分工模式、机器的特点等)和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的具体形式(居住模式、家庭结构、教育制度等);二、无产阶级的‘政治构成’是指工人把‘技术构成’转为武器,用以对抗资本。 他们以集体工作的连贯性作为自我组织的基础,从而把生产方式转为斗争方式。[7]
因此,“分解”在这两种意义上都可以指无产阶级构成的解体。《尾注》在《盘旋待降》提出了相关的 “(无产阶级)构成的问题”:
构成问题指的是在斗争过程中,组合、 协调或统一无产阶级分裂的问题。与过去不同的是——或至少与过去的理想典型不同的是——我们现在已经无法把阶级分化理解为一种可以自我愈合的现象,仿佛统一在某程度上也是“天然存在的”(如手工业者、大众或“社会”工人的统一)。今天, 这样的统一并不存在,也不能期望统一会随着生产技术构成的进一步变化而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存在已经预先定义出的革命主体。不存在“为自己”的阶级意识,也不存在对于所有工人共同利益的意识。又或者说,这种普遍利益的意识只会是资本的意识——正是这种意识对工人的分化,造就了工人的团结。
因此,阶级的构成问题在今天看来不是阶级内部的一个吸引点,而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如何在分裂的情况下,采取反资本主义的阶级行动?广场运动暂时搁置了这个问题。占领运动的优势在于,它在不可能的阶级斗争和不温不火的民粹主义之间创造了一个空间,让抗议者尽管存在分歧,但可以暂时团结起来。这使得斗争的激烈程度有了质的飞跃。但与此同时,这也意味着当抗议者遇到构成问题时,他们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自 1970 年代以来,过剩人口持续增长。从本质上讲,过剩人口的增长使阶级融合发生了逆转;融合变成了分裂。这是因为工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很低。由于每份工作都有很多人申请,管理者的偏见(例如某些“种族”比较懒惰)在决定谁能得到或不能得到一份“好”工作时产生了实际影响。因此,部分阶层的人被挤压在劳动力池的最底层。使这些人对某些雇主失去吸引力的因素,又使他们对其他雇主极具吸引力——特别是在雇员流动率高而雇主并不真正为此付出代价的工作中。大量过剩人口的存在为分离出一个极度受剥削的阶层创造了条件,马克思称之为“停滞的过剩人口”。这种分离强化了享有特权的工人的偏见,他们(在某种程度上)知道自己的“好”工作是基于雇主的偏见。这也强化了被排斥者的非阶级身份,因为正是这些身份构成了他们被排斥的基础。’
过剩人口、过剩资本
surplus population, surplus capital
“过剩人口” 和“过剩资本” 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发现的两个现象,属于“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的结果。在《尾注》第二期中《贫苦与债务》一文中,作者解释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掌握马克思这个核心论点的历史原因:从19世纪末到1970年代,马克思没有料到的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暂时对这两种过剩化的过程形成了反作用。到了1970年代之后,马克思原本发现的规律又变得越来越明显。《尾注》认为这个规律可以解释1970年代后全球资本主义世界的种种现象,包括TC提出的“阶级关系中的再生产危机”、“纲领主义”斗争周期的终结(即无产阶级为什么再也无法将自己阶级归属的肯定当作革命的出发点),还有《尾注》在《盘旋待降》等文中提出的“阶级分解/构成问题”。
简单点说,过剩人口就是无产阶级中资本再也无法用来剥削的一部分人口,这一部分远远超出了传统意义上的“产业后备军”,其社会性质和政治含义也不一样。随着生产率的发展、 “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趋势(主要在《资本论》第三卷分析),资本可以雇佣的劳动力也越来越少。与此同时,资本还被迫不断剥夺农民、原住民等原本可以在市场之外维持生计的群体,使他们如果没有机会给资本打工就无法生存。对资本来说,这些过剩人口只不过体现为社会维稳的问题,他们只需要被管理或宰杀,再也不是值得通过社会福利制度来维持生命的产业后备军。另一方面,同样的因素也导致了利润率漫长的长期下降趋势,因此可雇佣工人来生产剩余价值的投资机会越来越少。如果可大规模破坏“死价值”的世界大战不发生的话,这一系列的趋势就会使“过剩资本”以及长期经济停滞的现象不断恶化。在《贫苦与债务》、《盘旋待降》、《前进吧,野蛮人!》等文中,《尾注》使用了近几十年全球层面的统计,证明马克思在1860年代在逻辑推理层面上作出的预测终于开始实现,然后在此基础上对当代资本主义世界和无产者抗争趋势作出了政治分析。
种族化
racialization
“种族化”是指被统治的族群通过社会手段转变为“种族”的过程,人们相信“种族”具有某些固有的特征(无论是生物还是文化特征)——这种信念与相应的制度相结合,有助于维持他们的从属地位,并抑制不同种族化群体之间或他们与占主导地位的“种族”无产者之间潜在的颠覆性联盟。
在《尾注》第三期的《资本主义平等的极限点》一文中,作者Chris Chen写道:
在21世纪,美国种族化群体在失业和就业不足者中的显著过度代表——“最后被雇佣,最先被解雇”——表明了这些群体被让步性、不均匀地纳入了高度种族化的工资差异、职业隔离和不稳定劳动体系之中。随着资本在核心地区摆脱这些相对过剩的人口,全球北方由人数更少、剥削更严重的工人生产出的过剩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更低的工资,然后以来自全球南方的廉价劳动力的种族威胁形式重新出现。在美国,随着稳定雇佣劳动的结束和公共福利供给的撤回,一个庞大的“后种族”的国家安全体制已经成型,开始管理对国家面临的所谓文明威胁——通过监管黑人的无工资生活、驱逐移民劳工,并发动无限制的“反恐战争”。黑人大规模监禁的灾难性增加、美国南部边境的超级军事化,以及在穆斯林世界范围内继续进行的无限制安全行动,这些都揭示了“种族”不仅是相对经济价值的概率性分配,而且是对国家暴力不同脆弱性的指数。[8]
废除主义政治
abolitionist politics
“废除主义”一词本来在19世纪指的是主张废除奴隶制的运动,现在针对的是警察和监狱制度。警察、监狱制度的消灭一直都属于共产主义运动主张消灭阶级社会及其国家机器这一广大事业中的一部分,但是“废除主义”一词如此用法大概是从21世纪初美国学术界的批评性种族研究中开始的,并在后来2020年的乔治·弗洛伊德起义(George Floyd Rebellion)中获得了普及。在那场起义期间,参与者要求削减警察经费、将资金重新分配给社区资源、投资于其他社区安全模式,例如心理健康危机应对团队和修复性司法项目。因此,现在“废除主义”往往被理解为一种不同于共产主义/无政府传统意义上消灭国家机器事业的运动(有时候甚至是“改良主义的”的运动),虽然两者之间有所重叠。
在《前进吧,野蛮人!全球抗争与我们时代的“非运动”》,《尾注》的作者写道:
“削减警费”所设想的是,如果把花在警察和监狱上的钱都重新分配到其他公共服务上的话,就能够解决本该由警察来管控的潜在社会问题。但这么做忽略的是警察和监狱其实是最为廉价的公共服务,它们本身就是紧缩政策的写照,也因此这么做对解决再分配问题无甚裨益。从实操角度来看,“废除警察”常常意味着用其他机制来取代警察所扮演的角色(例如用专业的调解人员、社工和私家保镖等),但这么一来同样的弊病也可能会出现。但即便是更加激进的废除主义论调,在面对国家抛给警察的真正社会问题时也同样会犯错。【……】芝加哥的南部的凶杀率一度和巴西今年夏天的水平相当,对此我们可以更清楚地意识到废除警察却又不废除资本主义制度时情况会变成什么样。芝加哥大学位于海德公园,这里一块被该城市南部贫困社区环绕的富裕孤岛,那里的私人“警察”获得的经费比起周边所有辖区加起来的还要多。毕竟对于有钱人而言,私警终究是更加划算的安排:如果你想要的只是保护自己的财产,为什么还要把税金撒在保护整个城市的警力上呢?
性别、家庭的消灭
abolition of gender and the family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尔写道,“消灭家庭!连极端的激进派也对共产党人的这种可耻的意图表示愤慨”。废除家庭的呼声自那时起就一直伴随着无产阶级斗争,为性别解放和性解放提供了一种视野——它不断被其他策略和战术导向推迟和取代 。废除家庭的说法呼唤对日常生活的彻底、几乎不可思议的改变。对有些人来说,家庭是没完没了的恐怖,人必须逃离家庭才能找到自己的形象。对另一些人来说,家庭是抵御市场与工作的残酷性、种族主义警察和把人驱逐出境的官员的支持与关怀的唯一来源。对大多数人来说,家庭同时具有这两方面。没有人能独自在这世界上存活;一个人对自己家庭的个人态度,直接影响到他如何理解废除家庭的呼吁。【……】
家庭承载着在短促、异化的社会中生存的矛盾,它既是安慰也是绝望的来源。如今,废除家庭的口号已经成为对酷儿爱情普遍化(作为规范性制度的瓦解)的呼吁,以及朝向所有人的性别及性自由的迈进。家庭的消灭或许会体现为共产主义下真正的人类共同体中人性关怀的普遍化。
——《家庭会被消灭吗?》
正如我们大部分人的切身经历,在大部分女性的差别化自由被消灭之后,性别区分仍然持久地存在着。如果这种差别化的自由就是把女性束缚于市场间接中介领域的东西,那为什么它的消灭没有将女性从“女性”范畴和性别化的再生产领域中“解放”出来?【……】
去自然化进程确实使性别可能表现为一种外在制约。这并不意味着性别的制约比以前变弱了,而是说它现在可以被视为一种束缚,也就是一种在外在于自身、有可能消灭的东西。【……】如果现在我们真能将我们的阶级归属和性别归属视为外在的制约,那这绝不会是单纯的巧合。又或者会是巧合吗?这个问题对于理解以消灭性别为目标(即通过非性别化的个体实现生活再生产的目标,在这种生活里,所有分离的活动领域都被消灭了)的抗争来讲是关键性的。
——《性别的逻辑》
贱斥、市场直接/间接中介领域
abjection/the abject and the DMM/IMM spheres
在《性别的逻辑:领域的分离与贱斥的过程》一文中,作者借用了法国精神分析女性主义理论家朱莉娅·克里斯蒂瓦(Julia Kristeva)的术语“贱斥”(abjection、the abject)来描述被女性化的劳动及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性别领域。《尾注》的作者解释:‘我们想要从术语“abject”中挖掘的主要意义乃是它的词源意义:ab-jactare,即为被抛弃、扔掉的东西,但是,它仍是抛弃它的对象的组成部分……’
《性别的逻辑》把这种被贱斥为“女性”的劳动分析为“以市场为间接中介的领域的无工资部分”(the unwaged portion of the IMM【indirectly market-mediated】sphere)。最典型的例子是广义上的“家务”(包括照料小孩和老人)。虽然从事家务的人不收工资(因此意味着“家庭主妇”、“退休老妈”等身份不直接参与劳动市场),但这个领域之所以说是 “市场间接中介的”(而不是市场之外的),是因为她们所使用的生产资料(食材、房子、家用工具等等)主要是在市场上购买的,而且她们所生产的商品就是可以每天去出卖自己劳动力的工人。在现代历史上,家务一般被界定为“女性的本职工作”,而且女性从事大部分家务时并不领工资,虽然对资本来说,家务同工人在企业内从事的劳动一样必不可少(如果没人从事这些家务,工人阶级就无法完成再生产,从而就没人能到企业打工)。
在20世纪,随着资本的扩张以及对生活各个领域的“从属”(即吸纳、控制、变成可用来挣钱的手段),家务中的部分劳动类型逐渐被商品化(要么成为制造业的商品,如洗衣机、速冻食品;要么就成为服务业的商品,如家政公司、快餐店、幼儿园等等)。这样一来,家务中的部分劳动类型就转移到了“以市场为直接中介的领域”(the DMM【directly market-mediated】sphere)。同时,为了保证工人阶级的稳定再生产,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如在欧美20世纪中期利润率较高且国家收税稳定的时候),服务于资本的国家机器也会负责一部分原本属于“家务”的劳动(比如公立托儿所、敬老院等、医保等等),而这些劳动就会转移到“市场间接中介领域的有工资部分”(the waged portion of the IMM sphere)中去。因为这些“公共社会服务”是非盈利的,所以它是“市场间接中介的”而不是“直接中介的”;它需要付给员工的工资等成本是通过税收资助的,而且因为税收来自企业的部分利润,所以对资本的经济逻辑来说,这些服务算是纯粹的亏损,不是投资。通过把“家务”等再生产方面的任务外包给企业和国家,女性可以从无薪劳动的铁链获得某种程度的“解放”——虽然这往往意味着女性需要在外面打更长时间的工,特别是在再生产任务主要通过商品化外包给企业的时候,因为这样会提高工人家庭维持生存的成本。
但是,不管有多少“家务”等再生产方面的任务可以外包给企业和国家,总有一部分任务是留给女性(或从经济逻辑的角度来说,被“女性化”的人)不领工资就进行的。这个历史遗留下来的“余数”(remainder)就是《尾注》认为“贱斥”的领域,而文章的标题中所提的“贱斥过程”指的是:随着利润率的下降(这是全球资本主义从1970年代,尤其是2000年代以来的漫长趋势),资本及为之服务的国家机器就倾向于把越来越多的再生产任务从公共部门重新推到女性化无工资劳动的领域(这往往是“新自由主义紧缩政策”的主要内容)。这样一来,对原本开始享受某种“自由”的女性(或被“贱斥“为女性的人)来说,在劳动类型方面界定的“性别”就开始体现为一种外来的铁链,而不是自然的/传统的身份认同——与无产阶级的身份认同一样。因此,在当代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性别和阶级都开始被体验为需要通过共产主义革命来“消灭”的东西。[9]
左翼共产主义/共产左翼、博尔迪加主义、工委主义、极左派
left communism/communist left, Bordigism, councilism, ultra-left
“左翼共产主义”(指立场)或“共产左翼”(指组织)是一系列马克思主义革命传统,最初出自1920年代第三国际内部比列宁主义者更“左”的一些个人和团体,后来明确传承下来的传统主要分为两派:
一、以阿马德奥·博尔迪加(Amadeo Bordiga)为代表的早期意大利共产党,其“左翼”成员后来分裂成“国际共产党”。这个传统一般称为“博尔迪加主义”。
二、以赫尔曼·戈特(Herman Gorter)、安东尼·潘涅库克(Antonie Pannekoek)、保罗·马蒂克(Paul Mattick)为代表的“德国共产工人党”。这个传统一般称为“工委共产主义”(又译“委员会共产主义”,简称councilism “工委主义”)。
博尔迪加主义传统强调共产主义的内涵,认为在革命初期就应实现按社会需求进行生产和分配的原则,而不是进行过渡性的“国家资本主义”或所谓“社会主义”。他们主张反对任何形式的妥协,坚持革命目标的纯粹性和一贯性。
工委共产主义的最初源于马蒂克等德国和荷兰斗士由参与德国工人革命经验得出的结论。其核心特点是认为在工人斗争中工人自我组织的机构(即“工人委员会” workers councils,又称 “工人大会” 或用俄语词汇 “苏维埃” soviets)需要成为革命载体,替代工会、企业和国家机器来指导革命转型过程,包括期间的生产与再生产任务,直到反革命力量消失为止要形成暂时“无产阶级专政”的工人民主形式。
在1960年代以来的法国,“极左派”有时候是上述 “左翼共产主义” 严格意义上的同义词,有时候指更广泛的范畴,也可以包含其他反权威的马克思主义新思潮(如情境主义、自主主义、以及共产化思潮),还有各种无政府主义(即安那其/无治主义)传统。[10]
在1970年代,源于法国极左派的吉尔·多维(Gilles Dauvé)、TC等人和团体对博尔迪加主义、工委共产主义、情境主义几个传统进行了批判和选择性的综合,其中一部分团体开始用“共产化”这个词来表示自己与“左翼共产主义”传统的差别。到了1990年代,如本书《代序:访谈》所陈述的那样,英文世界的《扬弃》、《尾注》等团体在这种“综合性法国极左”的基础上发展了自己的视野。后者从英文学术界“开放马克思主义”(Open Marxism)[11] 的创意那里得到多元化探索的灵感之后,也开始添加来自种种无政府传统、意大利自主主义和德国价值形式理论的资源。现在他们一般不会自称“左翼共产主义者” ,而是直接用“共产主义者”(或者“自由/反权威的共产主义者”)来描述自己的视角。(现在“左翼共产主义”一般专指严格按照博尔迪加主义或工委共产主义的传统发展下来的组织。)
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情境主义国际
May ’68 and the 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
从1968年5月开始,法国爆发了持续七周的全国性动荡,以示威、大罢工和占领大学、工厂为特点。在后来被称为“五月风暴”的事件中,法国经济陷入停顿。抗议活动达到了一个让政治领导人担心可能引发内战或革命的程度。5月29日,法国总统夏尔·戴高乐秘密逃往西德后,国家政府短暂停止运作。这场抗议活动与全球范围内同时发生的类似运动联系在一起,激发了一代人以歌曲、富有想象力的涂鸦、海报和口号的形式创作抗议艺术。
动荡的开端是一系列极左翼学生占领抗议活动,抗议资本主义、美帝国主义和传统制度。警方对抗议者的严厉镇压导致法国工会联合会呼吁同情罢工,这一呼吁迅速蔓延,吸引了一千万工人参与,占当时法国人口的22%以上。这场运动的特点是自发的、分散的野猫罢工性质;这导致工会和左翼政党之间产生了对比,甚至有时发生冲突。这是法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总罢工,也是第一次全国性的野猫罢工。
情境主义国际是一个由先锋派艺术家、知识分子和政治理论家组成的国际组织,活跃于1957年至1972年期间,主要在法国等欧洲国家(但是香港等地方也有成员和相关刊物)。它的思想基础主要源自反权威马克思主义和20世纪初的先锋艺术运动,试图将这两个领域综合起来,形成对20世纪中叶资本主义的全面批判。情境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是“景观” (spectacle),即一切直接生活都沦为表象,一个只能被看待的独立虚假世界,这种世界观将人类社会生活与外表联系起来,导致商品和图像被认为具有自主运动性,社会生活则被否定。[12] 它第二个重要概念是对抗景观的手段:构建“情境” (situations),即有意识地构造生活的时刻,以重新唤醒和追求真实的欲望,体验生活和冒险的感觉,实现“日常生活的解放”。[13]
虽然情境主义者起初主要强调艺术和理论方面的活动,但到了晚期(1968年前后),其焦点就逐渐转向基于工委共产主义纲领的社会革命。在1967年,该组织出版了两部最有影响力的著作:居伊·德波的《景观社会》以及鲁尔·瓦纳格姆的《日常生活的革命》。这两本书似乎在五月风暴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引用情境主义著作的口号在法国的涂鸦和海报中随处可见。此外,该组织的成员还积极参与了起义,试图协助创造能够打破资本主义日常生活秩序的“情境”,给学生和工人提供联合起来的机会,希望他们能形成工委主义意义上的“革命委员会”。总体来说,情境主义国际对共产主义理论的主要贡献可分为两个方面:在社会分析上,(相对于传统工委主义和其他法国极左派)它通过“景观”等概念的分析更强调资本主义对整个社会、文化、城市规划各个方面的控制;在革命的视野上,它首次提出“想象力的解放”,包括要消灭“工作”和“闲暇”之间的隔阂,认为共产主义的目的之一是要延长闲暇的时间(没有必要浪费时间在打工上)等等。
警察的暴力镇压以及主流左翼机构的机会主义妥协最终共同导致了五月风暴的解散。法共在运动期间虽然支持罢工,但对学生运动表示了谴责。法共甚至组织了纠察队防止工人和学生混在一起,法共因此被认为是“斯大林主义的党”。法国总工会也明确拒绝暴力夺权政权的做法。这场起义的爆发与解散、情境主义国际等极左团体在其中在理论与实践上的探索、以及接下来1970年代法国出现的新型工人斗争,共同促进了法国极左派的反思与争论。这些争论最后为TC等团体的“共产化“思潮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影响了法国工委主义者、安那其主义者等其他极左思潮后来的发展。大家纷纷分析五月风暴为什么会出现,为什么会失败,它代表了无产阶级斗争趋势的什么新格局,未来应该如何介入等问题。[14]
价值形式理论、系统辩证法
value-form theory, systematic dialectics
“价值形式理论”是一个总称,包括一系列以马克思在《资本论》使用的分析法为基础的思潮,涵盖俄罗斯、日本、德国和英国理论家的作品,其共同点是批判了社会主义第二国际(1889–1916)以来对《资本论》的肤浅“正统”误解,以及相关的整个进步主义、发展主义世界观和政治视野,并重新使用黑格尔的“系统辩证法”来阅读马克思的德文原著(包括《资本论》几卷没有来得及发表的草稿)。他们发现“价值”、“形式”、“辩证法”这几个核心概念的意义与正统的理解很不一样。在本书第一卷的《共产化与价值形式理论》一文里,《尾注》主要介绍了“新马克思解读派”等德国1970年代以来的价值理论探索及其社会背景,并且探究了它们可以对(之前没有怎么注意这种学术界产物的)共产化政治提供什么样的贡献:
价值形式理论的批判意味在于,它质疑所有以肯定无产阶级是价值生产者为基础的政治认知,且它承认马克思的作品本质上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否定批判。价值形式理论在重构马克思的价值形式辩证法的时候展现出社会生活过程如何从属于,或者说“被形式规定”在价值形式之下。这种“形式规定”的特点,在于反常地认为形式比内容优先。劳动不仅是在自身被对象化到资本主义商品中之前就存在的非否定的基础,有待通过调整形式的表达,从而在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那里解放出来。【……】
我们用劳动生产资本这一说法虽然似乎是真的并且在政治上很有效,更精确的说法其实是:在这么一个上下颠倒的世界,我们作为劳动的主体是被资本生产出来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价值的尺度,只是因为价值形式将劳动设定为自己的内容。如果社会不再受异化的社会形式宰制,且不再以抽象财富的自我扩张为取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典型的强制劳动就会消失。抽象劳动这个范畴将与价值一起消失。个体和个体需要的再生产将以自身为目的。没有了价值、抽象劳动和工资的范畴,“劳动”将不再具备受首要的社会中介所规定的系统性作用,而这个中介,就是价值。
这也就是为什么价值形式理论在谈及从其出发的革命的理念的时候,其实和共产化是一个方向。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超越不能仅仅停留在“劳动的解放”上;相反,这里唯一的“出路”是消灭价值本身——消灭将抽象劳动设定为财富的度量的价值形式。共产化是要摧毁商品形式,同时在个体之间建立无中介的社会关系。如果将价值理解成是社会中介的总体形式,那么对价值的大扫除就不能半途而废。
工人主义、工人调查、自主运动 / 自主主义
operaismo, worker inquiry, Autonomia, autonomism
意大利的 “工人主义”(operaismo)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整个60年代,是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工人运动中的一个流派。它提出了针对工人斗争的新型理论和实践方法,包括:
一、将生产现场的斗争设定为共产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中心;
二、采取了“共同研究”(conricerca,又译“工人调查”)的介入方法(即左翼知识分子与工人合作进行研究,调查工作场所条件和斗争);
三、提出了“阶级构成”(class composition)相关的一套理论,作为理解这些条件和斗争的框架;
四、通过工人调查和重读马克思作品,得出了关于资本主义技术的结论(即技术不是中立的,而是资产阶级统治工人的工具);
五、认为历史主要由工人“拒绝工作”(refusal of work) 等反抗行动推动;
六、强调工人阶级的“自主”(autonomy,又译为“自治”)和自我组织,与工会和政党等官方代表相对立。
工人主义的代表性理论家包括马里奥·托仑蒂(Mario Tronti)、拉尼埃罗·潘齐埃里(Raniero Panzieri)和早期的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后者于1970年代放弃了工人主义立场,成为自主主义重要的理论家。
工人主义为1970年代初出现的“自主运动”(Autonomia)及其“自主主义”(autonomism)理论奠定了基础。后者更强调工人运动在工作场所之外的自主和创造力(包括女权运动、学生和失业者的斗争),反对整个社会的组织形态(包括学校等再生产领域的制度),并将其分析为“社会工厂”。(部分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提出家务劳动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有所贡献,这个观点就是源于该运动,他们还在该基础上开展了“家务劳动工资化”(wages for housework)运动。《尾注》对此概念的批判可见《性别的逻辑》和术语表中关于“贱斥过程”的说明。)
在1990年代,一些国际团体,如成立于德国的科林科(Kolinko)小组从自主主义传统中脱颖而出,但也否定了该框架部分内容,比如后者转而不参与工作场所斗争)。这些团体复活了工人主义的遗产,并注入新的重点,比如在工人调查的实践方面,他们认为不仅要“与工人一起进行研究”,还要自己成为工人(或者说不要否定自己就是工人),在战略性重要领域进行基层工作,从而更好地了解工人状况,与其他工人建立关系,并在斗争开始时作出贡献——他们呈现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时的身份不是先锋党,而是“工友”。在本书《代序:访谈》中提起的“愤怒工人”(Angry Workers)国际小组,属于目前正在发展这种当代工人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一个代表性团体。[15]
“工人自主”(由诸多团体、刊物组成的运动,1973-1979年)Autonomia Operaia 又名“有组织的自主”(Autonomia organizzata),有时直接简称“自主”。在 1970 年代初,“工人自主”替代 “工人力量”,成为当时意大利诸多社会和政治运动中最具 对抗性、最暴力(尽管不是恐怖主义式)的运动之一。自 主主义者坚信工厂工人自始至终作为革命主体的重要性, 但他们也承认,其他吸引着意大利新一代战斗分子的斗争 领域(包括性别、性向和种族)具有与日俱增的重要性。 因此,“自主”较于“工人力量”在理论和事件上都比较分 散。“工人力量”解体后,奈格里加入“自主”并撰写了几 份讨论其组织方案的小册子。其中,“社会工人”(这是关 于弥散在成为“社会工厂”的全社会的新无产阶级的假说) 概念影响尤甚。1970 年代末,“工人自主”的地位被更新的运动所替代;它也和这些新兴运动一样,主要是被国家的直接镇压和集体判刑而摧毁。’[16]
作为一个更广泛的概念,在 1970 年代意大利的工运、 女权等社会运动有关的马克思主义话语当中,“自主”(也可译为“自治”)指的是工人、妇女、学生等无产群体积极 去反对被代表,反对自称代表他们的传统工会、政党等左 翼组织,而独立地直接行动(比如进行野猫罢工)。 有一部分自主主义者强调,虽然都属于无产阶级,但 不同群体之间还是存在不同的利益冲突。某些群体(比如来自大城市的中年男性技术工人)往往试图代表、代替或 忽略其他群体(比如年轻的农民工、女工、家庭主妇等), 所以他们主张无产阶级中的不同群体还需要把自己的具体 情况和问题分析清楚,从而自我直接行动。’[17]
回到本书主页
[1] 注:本书以粗体表示读者可于术语表中查阅说明的术语,以底线表示强调,两者皆为译者所加。
[2] “Bring Out Your Dead,” Endnotes 1 (2008). 刊名的另一个解释是成员讲的一个笑话:从《扬弃》分裂出来成立《尾注》的成员正好是那些原来负责写注释的人,之后离开时,他们也把注释一起拿走了。
[3] “Crisis in the Class Relation”, Endnotes 2 (2010)。这在第二期出版之前就单独发表过,可说是《尾注》小组最早表达自己立场的专著(第一期主要是翻译并评论TC和多维的作品)。
[4] “Bring Out Your Dead,” Endnotes 1 (2008) 。
[5] Théorie Communiste, “Much Ado about Nothing,” Endnotes 1 (2008)。
[6]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资本论 (1863-1865 年手稿)》摘选,第六章: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人民出版社2009)。《尾注》对TC,卡马特和奈格里对这两个概念的使用的总结和批判,见 “A History of Subsumption,” Endnotes 2 (2010)。
[7] 引自《无产阶级闹天宫:意大利六七十年代的阶级斗争与理论探索》第二卷(DGT 2018),第166页 <gongchao.org/cn/gongrenzhuyi-ji-qi-pipan>。
[8] Chris Chen, “The Limit Point of Capitalist Equality: Notes Towards an Abolitionist Antiracism,” Endnotes 3 (2013)。
[9] 又见“性别的消灭” the abolition of gender、“无产阶级的自我否定” self-negation of the proletariat、以及“形式/实际从属” formal/real subsumption。
[10] 英文语境里,ultra-left 这个词一般具体指法国的思潮及其组织(或者是中国文革时“湖南省无联”等比毛主义更“左”的历史现象)。至于法国和中国之外的左翼思潮分类,最接近的英文对应词大概是“反权威左翼” (anti-authoritarian left),然而,部分共产主义者和安那其主义者不会自称为“左翼”(他们认为“左翼”只能代表资本主义政治领域的左翼,即国家议会中的种种左翼党),所以一般只会尴尬地自称“共产主义者和安那其主义者”,或者干脆说“同志们”。“激进左翼”(radical left)比“极左派”还要广泛,一般也包含各种列宁主义传统。
[11] 关于“开放马克思主义”(Open Marxism),见《代序:访谈》。
[12] 居伊·德波《景观社会》(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guy-debord-1967),第一章。
[13] 鲁尔·瓦纳格姆《日常生活的革命》(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
[14] 关于情境主义国际与五月风暴的关系,见《时代之始:法国1968年5月占领运动中的愤怒派和情境主义者们》(DGT 2019)。关于该运动的中文学术研究,见《五月之后:法国68年的绵延于遗忘》,摘于《直到胜利:全球的一九六八》(DGT 2018)。
[15] “愤怒工人” 小组写的部分工人调查报告已有中文译文,如《别崩溃,宁愿怠工!》, libcom.org/article/biebengkuiningyuandaigong 。科林科的文库在 nadir.org/nadir/initiativ/kolinko 。
[16] 《无产阶级闹天宫:意大利六七十年代的阶级斗争与理论探索》第二卷,第188页(DGT 2018)<gongchao.org/cn/gongrenzhuyi-ji-qi-pipan>。
[17] 同上,第1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