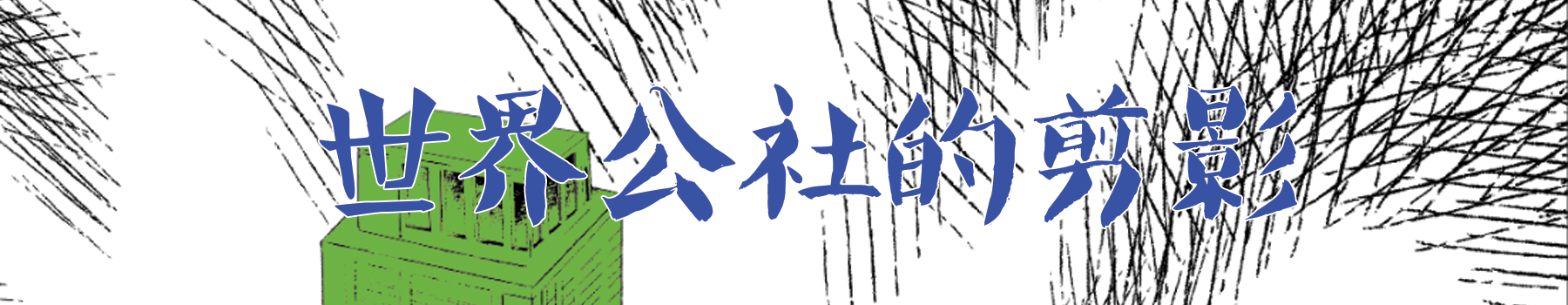
世界公社的剪影[1]
无阶级社会之友 著
1 妄自狂想[2]
多年以来,宣称“不同的世界是可能的”这种说法只通过两种形式的信息展现,一种来自墨西哥的拉坎东(Lacandon)雨林,一种来自那些认为创造新世界不过是引入某种新的金融交易税的人。2008年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袭击市场的时候,这一切很快改变了。自那时起,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草图就极大丰富地出现,有些还成了畅销品。极端派也不断前仆后继,重新思考事情还可以怎么发展。当下人们讨论的这些替代方案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它们是在桌上草拟出来的,不是在街上孵化出来的。从最近的斗争(占领华尔街运动、阿拉伯之春,或者南欧反对集体贫困的抗议)塑造出如此构想这个层次来看,这些构想大多是以否定的方式塑造而成的。倒不是因为这些斗争最终失败了,而是因为这些斗争大部分发生在生产领域之外,坚持要达成“实际民主”。结果,这些斗争几乎没有引出新社会的问题。
第二国际关于大罢工的争论和工委共产主义理论虽然不光是实际斗争的反映,但也指涉了这些斗争——“苏维埃不是一个理论的发现”(德波)。不过,今天对新社会的各种灵感似乎不过是抽象的空想主义,并且恰恰是从马克思到法兰克福晚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禁止圣像”(Bilderverbot),这一整个批判理论家流派抗拒的那种主义。这一个思想流派认为空想主义是狂妄的心理幻想,坚持要留待自我解放的人民决定自己集体生活的新形式。法兰克福学派反对现成的“解放社会”大纲,以纯抽象的方式与现状相对立,从而正确地坚持从具体的社会矛盾出发:只有无产阶级自己,才能通过漫长的阶级斗争最终建立新社会。共产主义不应该是理想,而应该是“实际的运动”。
不过,“科学社会主义”本身承认空想派具有“处处突破幻想的外壳而显露出来的天才的思想萌芽和天才思想”(恩格斯),最终却具备了意识形态的特点,以致于将历史规律引述为胜利的担保这种程度。这种历史乐观主义最近是在1914年彻底身败名裂,却在继续启迪当代理论。这些理论不为过去和现在的灾难所动,要么继续希望将来的斗争会自动展开、所有事情接下来会跟进,要么宣布生产力的发展是历史的引擎,最终历史能实现美满的结果。革命自发论党人对全球工人阶级的增长从来不失信心,而技术发展反正能通往解放这种错觉,也已经披着数码的喜乐外衣卷土重来。
如果不将革命看作完整的奇迹,看作无产阶级在高潮一刻几乎是偶然地、自发地达成的革命,并且没有预先设置任何目标,如果不将人类解放的规划指派给机器,那么就有理由去尝试针对无阶级社会的基本特点达成一点理解。对此已经有多种反对意见:为时尚早(“斗争还没到那水平,时未到”),没有必要(“人民最后能处理好的”),装腔作势(“你怎么能提前规定好”),或者就是不可能(“你怎么能料到这个”)。但是,从来没有一场持续的运动在违背现存秩序的时候,不具备一个可以用什么取而代之的理念(不论有多么模糊)。某些极端左派呼吁的对现状的纯否定批判最终是不可能的。比如说,目标定为“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资本论》),这必然出自对私有财产的批判。但是,因为这个目标留下了许多想象的空间,包括那些与自由和幸福毫无关系的情景,所以革命派应该宣明自己想要什么。这不是为了淌救赎配方的混水,而是为如何抛下旧世界的必要讨论作出贡献。不应该将公社认知为终结人类一切问题的东西。相反,只有在革命生产关系以后,今天用盲目的中介、统治和强力去“解决”的一切事物,才能开始显现为需要解决的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之上,本雅明否认了他将共产主义绝对化为“人类的答案”的指责。相反,他将共产主义冷静地描述为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要“以这个系统的可行成果作为手段,为人类消灭非生产性的答案的伪装;诚然,这样做是为了完全放弃“总体”系统的狂妄前景,并且至少尝试用一个晚上睡得很好、开启新一天的理性人那种松散的方法,去建构人类的时日。”[3]
2 哥达纲领批判的批判
许多近期的后资本主义社会大纲倾向于“冻结”社会想象力,将其定格在对应1875年的水平。那时候火车已经开始在全球喀嚓前进,欧洲工人运动也达到了某种程度的组织,但是,那时候的生产力和今天相比是微不足道的。现代的雇佣劳动阶级在世界的大多数地区还不存在,就连欧洲的居民也大多是农民,遍地文盲。马克思为什么在《哥达纲领批判》里将共产主义分为两个阶段,大家可能明白或者不明白。第一阶段,人们的社会财富份额依然由贡献的工时所决定,只有在第二阶段(生产力这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才能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和消灭国家。鉴于1875年以来发生的巨大变化,这样一个“第一阶段”在今天是否必要甚至应否追求,需要重新考虑。不是只有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孤儿在依附在按照工时分配产品的概念,许多反威权左翼也依附着。就连那些相当现代的构想,委员会被冠以“反威权中心”的名号以后,每一名公社社员也必然有一张“时间表”要填满。
这个模型不能简单忽视为通过其他手段来延续雇佣劳动:生产资料当中的私有财产会被社会计划取代,劳动力不再是一个商品,在竞争市场上随意买卖。这个模型还假定严格的平等,认为不论是大脑手术医生还是石匠,他们的每个工时的价值是相同的。不过,从产品分配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来说,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还是清晰烙下了“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每个工人“从社会方面领得一张证书,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为社会基金而进行的劳动),而他凭这张证书从社会储存中领得和他所提供的劳动量相当的一分消费资料。”(马克思)只有在社会主义之下,被资本主义下降为闹剧的等价交换才能真正实现。当然了,不是所有人都会领得和自己的贡献完全一样多的东西——总产品有一部分要用在新生产资料、一般性公共规划、育儿、养老和治病的花费上,但是不会再有剥削。到今天位置,以电脑化计划为基础的最为详尽的“新社会主义”模型也只是停留在这个水平。
人们可能抗议说,只要等价交换还在,共产主义就不存在。早在1896年,彼得·克鲁泡特金已经抗拒“所有属于生产的东西成为公有财产,但是人人都应该根据他在生产中消耗的工时来结算劳动支票”,他认为这个模型不过是“社区式工资结算和个人式工资结算之间的妥协”。马克思认为这在某个阶段是“无法避免的”,但是从来没有否认其中的瑕疵,他最终从长远出发,以最终打破被等价交换界定的视野的社会为目标。但是,鉴于“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在革命之后会更充分地涌流,现在坚持这种二阶段模型难道不是不合时宜?处在这么一个时代,世界充斥着越来越少的农民和越来越多的高校学历失业人员,为什么还要死守这个观点?这是根本的问题。
和过渡阶段相关的场景推演,似乎至少可以带来一点现实主义。这些推演没有理所当然地认为革命后马上存在完全的社会和谐,而是将今天实际状况中的人作为出发点,也就是将他们当作总体自私的人,要得太多给得太少。但是,一旦人们往深处想,如此模型表面的现实主义很快就会瓦解。当然了,公社内要有合理计划的生产,至少都要我们含糊地认识到要多少劳动才能有成果。比如说,建造一栋公寓楼需要一定数量的人劳动一定的月份,但是,将个人消费捆绑在执行工时数之上完全不是一回事,因为这样就假定了我们可以将用于产品制造的确切时间量化出来。即使用最精细的记帐法(这已经需要多得荒唐的时间和精力),就算计算的是最简单的产品所体现的工时,也是极其困难的任务。比如说面包卷,不但要知道造烤炉用了多少工时(背后投入了一连串的初步产品),还要知道烤炉会运作多少年,这个期间能出炉多少面包卷。再者,我们越是考虑运输手段和所有其他生产的前提条件,任务就越是艰难。如果考虑上科学在生产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应用,这个任务直接成为不可能。比如说,应该预留多少秒来写用于生产链不同节点的软件?用于所有生产过程的总体的公有社会知识,又该预留多少?小资产阶级物物交换俱乐部里的概念——A替B的草坪除草1小时,B替A洗大众车来回报——在以劳动与技术的高级分工为基础的社会生产水平那里,完全不可能应用。任何这种尝试需要持续追踪时间,依然注定失败。如此理解的共产主义会成为资本主义市场的可悲临摹,劳动时间的规律会以盲目和混乱的方法驰骋。
除此之外,这个模型还建立在劳动与非劳动的严格区分之上,这不但看起来相当乏味,还会要求对今天以盲目力量运作的某种东西进行行政规范。就其定义来说,劳动是要结算的,并且只在劳动似乎有利可图,又或者被国家认为是必要的时候才需要结算。所以在上述的“第一阶段”,公社就得将每一项社会活动分为这两类中的一种,以便度量工时。这样分类会随之带来各种随意的决策。比如说,酿酒和喝酒各自可以很容易区分为劳动和休闲活动,但是智力活动就会难得多。如果涉及再生产领域,那就几乎不可能区分,因为这个历史上主要归于妇女的领域已经激发了关于劳动概念本身的无穷争论。照顾小孩的一小时可以归到“时间表”吗?还是说只有常规照顾一大群小孩才算数?更一般来看,按照这种范畴来划分生活有多大吸引?另外,这种模型高度依赖的资产阶级社会基础所遗留的这种心理,在考虑人们工时的时候,很有可能无力劝阻大家作弊。监查每个个体的表现的机制必不可免,即便这个模型的提倡人不愿承认这种必要性也是如此。就算“时间表”和工资制度不同,也还是由强制所支撑。这种强制和所谓意识改变的目标截然对立,这个目标不能从革命第一天开始就当作理所应当,而是要从一开始指向所有革命活动。
所谓社会主义“第一阶段”的现实规划是依附了矛盾的前提:一方面预设了人们偏爱自由联合,另一方面这些人又被原来的好东家精神所鼓舞,渴望占其余所有人的好处。社会革命如果从起步的时候就不按照新原则行动,不将所有劳动义务化,同时(尽可能)将劳动转化为“诱人的劳动”(travail attractif),让所有人自由获得所有商品,并由社会重新吸收国家权力,那么这场革命会再一次承受风险,可能错失创建自由社会的机会。所以,马克思所说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是特定于某个历史时期的,也即出于权宜。但是,拒绝过渡性社会的理念并不意味着梦想一夜之间就蹦出个公社。当然了,这种转变会是一个无聊漫长的过程,还会伴随敌对和倒退。不过,比起死守一个世纪以来除了马克思的许可盖章就一无所有的模型,革命派最好还是为今天的革命勾勒好状况,至关重要的是勾勒好生产力发展的状况。[4]
3 共产主义对机器的使用
对现存社会关系的共产主义批判在传统上会以这么一个前提出发,就是要推翻生产关系,从而将资本主义发展起来并物化为机器的技术生产力从私有财产的桎梏那里解放出来,这样生产力就能为具备自我意识的人类效劳了。不过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840年代就注意到,资本推动的发展最终会达到这么一个阶段,“生产力和交往手段在现存关系下只能带来灾难,这种生产力已经不是生产的力量,而是破坏的力量”(《德意志意识形态》)。正如马尔库塞注意到了某些“统治的特殊目的和利益并不是‘随后’或外在地强加于技术的”,这些目的和利益“进入了技术机构的建构本身”,工人自治主义者拉涅罗·潘齐耶里(Raniero Panzieri)也引用了马克思,将现有的技术批判为使活劳动服从资本命令的手段。产生剩余价值的目的并不外在于机器,而是和塑造劳动过程的总体性一样,构成和塑造了机器的方方面面。
应该关注这个想法。一方面,“自动化工厂有可能建立起互相联系的生产者对劳动过程的统治”(潘齐耶里),因此是没有稀缺的自由社会的前提。另一方面,现代工厂制度的机器显现为“主体,而工人不过是有意识的器官,和自动机的无意识器官共同协作,而后者要服从中心的运动力”。于是,机器的资本主义式使用不仅显现为对“客体”的扭曲或者偏离和基本理性的发展过程,这种使用还规定了技术进步本身的发展过程。这在烟囱还在冒烟、机器还用来取代人力的时候,和在零件和芯片时代、代码理应取代工人的智力的时候一样成立。在现有条件下,数码技术和模拟机器都充当从上而下的阶级斗争的手段:这两者的目的不是改善生活条件,而是催生对人类劳动最有效率的剥削。具体来看,这两者规定了劳动的节奏和生产的组织,保证了雇员符合规定,最终得以摧毁所有人际间的联络。通过在所有生产领域强力推行极其碎片化的工作流水泰勒制规划,这两者大大推动了商品劳动力的贬值,最后促成工人的议价力削弱。除了这种削弱之外,那些依赖工资的人还屈服于马克思所描述的“工厂的专制”之下。工人的地位进一步贬低了,现在不过是“智能”有网络的机器的附属品。他们被优化过程的软件推动,一开始会体验到空虚、压力和过劳。他们连最少量的自由都被抢走了,有时候还包括生产过程的任意一点知识。
如今的工业4.0已经可以看到左翼电脑爱好者所发现的新生产模式的“细胞形式”,其实从更高层次来看,这是资本对劳动的凯旋。数码新“行动选项扩大了工人对自身活动的状况的支配能力”(斯蒂芬·梅雷兹)(Stefan Meretz),这种想法在所有亚马逊的工人耳里一定是恶心的笑话。这种情形,再加上在目前摧毁性力量的发展状态之下,尽管代价是摧毁整个世界,但是只需要少数资本家就足够维护现状,这两点对那些将这种发展看作不过是精英对社会运动,对所谓不服从的下层阶级进行的技术攻击的人来说,并不陌生。这种理论趋势的一个弱点,是不认为资本主义要为当下技术发展的形式负责,将罪责归于一小撮掌权者,高估了他们无上的行动能力,即便这种个人和他们的策略当然存在也是如此。只是,这种立场确实准确阐释了(数码)技术的一个功能,但是这样的后果是防御性十足的纲领,旨在劫持和摧毁,而新技术对共产主义社会的潜力几乎没有考虑过。
和每个新生产力一样,“数码革命”有时候指向可能超出了现存的生产力,和既定的生产关系和所有权发生矛盾。遏制不断增长的计算力的潜力,这些“创新”就是资本作出的回应。在软件工业,多年来有大部分的研究投入到了在数码领域执行商品形式。除此之外,个人电脑也不再是“通用机器”了,它们的可能性受限于安排好的界面和程序,以至于它们只能发挥数码资本主义终端的作用。这种做法被正名为“用户友好性”:现在任何使用电脑的人,如果使用缘由超出研究、开发和生产,就不应该再去明白装置的原理,而是被引导去适应数码服务。和资本主义之内的大多数生产力一样,电脑的发展历程有个特点,用户在和电脑打交道的时候没有学到任何专属于生产力的技能。相反,我们陷入这样的境地,电脑的广泛使用带来了社会退化;认为智能手机需要更愚笨的人使用,这一种文化悲观的怀疑情绪并不是那么不着边际。
革命运动必须既不提倡今天这样的社会主义大规模生产电脑和智能物体,也不提倡盲目摧毁技术,而是要朝着这些技术的内在潜力而努力。一方面,这就意味着将使用技术必不可少的知识扩散开,另一方面还意味着将唯一目的是服务于生产剩余价值的使命、将这些使命变得无害的机器之中的那些要素辨认出来。重点不仅是消灭所有权的头衔,还是重新夺回社会对技术的控制,这将意味着深度转变现有的机器来满足人们的需要。[5]
4 稀缺与热情
稀缺不再是生产财富的手段不足的结果,而仅仅是现有财产关系引起的。考虑到这一点,监控个体的劳动表现的做法就变得更可疑了。尽管公社会获得规模巨大的生产力,但是当然依然有可能出现瓶颈。不过,瓶颈不会因为采用时间表就消灭。诸如此类的控制系统实际上会不必要地捆绑能量,妨碍创建“自由人的联合体”和“社会性个人”所必需的意识转变。共产主义革命的成功或许最终要依赖这种意识转变。在自由社会才能充分发展潜力的生产力,必须将人本身纳入其中一部分。此处适合回顾傅立叶到马尔库塞的思想家,他们将解放社会理论化的时候,认为“热情”在没有强制的时候会富于生产力。
根据不同的社会学研究显示,全球技术和经济发达地区的雇员最优先考虑的是工作有趣、有意义,并且承担责任。正如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指出狗屁工作的时候表明的(这些工作蠢得会让任何一个有点理智的人完成以后,内心充满羞耻而不是骄傲或者满足),资本主义无法满足上述的需要。这些工作在公社会消灭。其他会自动化。剩下的会尽可能转化为诱人的劳动,也就是与其他人自由联合完成,而不是听老板命令完成;就是帮助发展工人“感官、能力和反射机制”(Meinhard Creydt)的工作,不是只以产出最大为目标的工作。最后,即使是无聊的岗位,如果能够轮换,从而只在短时间内进行,那也能够接受。
当然了,钢铁生产不能就这样变成玩乐。但是即便如此,自动化的繁荣在劳动力萎缩的情况下依然导致全球过量生产。不过,“热情”如果用来监控大半自动化的流程而不是解决棘手的问题,也就不那么富于生产力了。社员不应该建立一套控制系统来防止人们怠工,而是要致力以平等主义的方式,组织和传播实践与理论知识、教育和所有社会领域之中的技能。即便是今天,熟练工人的生产力依然高于非熟练工人,这样的共产主义还不如工厂工人的共产主义。相反,每个人的能力都应得到发展,这样诸如机械工程、医药、交通服务或者计算机科学的领域也能向他们开放。到那时候,尽快超越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分野必须从一开始就成为革命运动的指引原则:成为业余爱好的体力劳动——艺术和手工业、城市园林、模型制造、修理旧车等等——它们数量之大令人瞩目,表明了用自己双手去做一件事情多么有“富有生产力”的热情。目标不应该是最公平地分配劳动和自由时间,而是在最大可能的生产自动化之下人道地废除这种分离。[6]
5 狗屁工作
尽管消灭愚蠢工作具有前所未有的潜力,但是人类技术性消灭工作的古老梦想在所谓数码时代也不会实现。怀疑派援引得最多的是护理工作,以此证明自动化的局限。但是,农业也是同样重要的例子,对于农业,公社将来首先要推翻许多引发了灾难性后果的生产力进步成果。这彰显了一个不愉快的事实:公社不但要从资本主义那里继承科幻般的生产力,还有堆积如山的未解决难题。1871年的公社当然不懂电脑,但是他们也不用担心地球会遭遇无法逆转的毁灭。20世纪批判理论的轨迹揭示出,人们除了生产关系,也越来越关注生产什么和生产有什么后果。1950年代的情境主义者可能是第一批看重城市被自动化交通摧毁的革命派,也是第一批在纲领中呼吁消灭“寄生行业”的革命派。
对公社而言,规定了大都市日常生活的那些无意义甚至有害的活动所组成的无尽清单,一开始似乎是馈赠,因为消灭这些活动立马会解放大量的时间,一个个产业倒闭,更多的人由此可以完成既不能自动化,也不能转变得更加有趣的任务。但是,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自身的非理性已经将人类的整个新陈代谢渗透到自然当中,并且在空间当中将自己具体地实现出来。如果要找鲜明的例子,请看完全没有解决的能源问题和“城市碎片化为农村”(德波),看那些恶名远播的城市蔓延,看它们苍白的非处所如何用小规模开发的同时将使用汽车变得必不可免,从而加剧了能源问题。公社不但要发明新的能源供应,还极有可能要花费很长时间摧毁这些非处所,修复南方世界的贫民窟,重新打造农业和恢复降解后地区,同时可以不用太依赖机器人完成这些任务。这不是在其他领域不穷尽自动化的可能的理由,特别是在廉价劳动力使自动化的吸引力下降的全球贫困地区,确实,自动化会解放清洁的人力。但是,新技术降临以后真实的丰饶就落在人类身上的预期就会因此削弱,而这仅仅因为数码商品可以无限复制,吹风机现在可以联网与烤面包机通信了。[7]
6 需要和公社奢侈品
公社的财富几乎不再是我们所认识的财富,不是只在不同的关系之下生产的财富。大都市的居民已经拥有的航班、汽车、手机,以及丑陋的廉价T恤,这些再多给他们也没有意义。这也不是因为这些需求可以指责为“人造”需要,与所谓自然需要相对立。正如法兰克福学派的晚期马克思主义者所表明,区分人造需要和自然需要往往具有威权主义意义之上的武断趋势,因为在个体欲求之中彰显出来的自然在每一种需要之中都与社会紧密交结。但是,需要之为现存阶级社会的产物并不无辜,也不一定理应投射到无阶级社会。对这个困境,阿多诺一方面用自己论点的辩证法核心来回答:重新组织生产来满足“均平的、尤其是资本主义生产出来的[需要],那么这些需求本身会遭到决定性转变”。有一点将会“迅速表明”,就是群众如今不需要强加给他们的“垃圾”。另一方面,阿多诺用平等和团结的理念来回答:“直接满足需要的问题并不是以社会和自然、主要和次要、正确和错误的角度提出的,相反,与这个问题碰撞上的是地球上全人类的绝大多数人受苦的问题。如果我们生产的是全人类最迫切需要的东西,那我们就会免除这些需要的合法性所引发的高企的社会-心理顾虑。”
由于那些最迫切又没有满足的需要程度之深,特别是在南半球的需要,再加上自然恢复力的限制,世界公社不得不在全球范围重新打造许多东西。这不是为了让各个地方的东西看起来都一样,按照今天的标准,一定有地区被认为“拖后腿”,也就是技术和工业不发达。但是,为了应对世界的贫困地区几乎一穷二白,没有住房、医院,甚至没有下水道的情况,又不毁灭地球的恢复前景,旧资本主义中心的能源和资源消费必须大幅降低。尽管全球的无产阶级生活条件有某种同化的趋势,但是德国依赖社会福利的人比亚洲任何一个纺织工人依然明显活得好,西欧平均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依然是非洲大陆居民的均值几倍之高。
社会革命运动不会提出“真”“假”需要的问题,也不会披上绿色的外衣施行任何紧缩的反享乐主义做法,而是要在资本主义中心以另一种财富为目标。如今财富本身展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并没什么社会性质,只不过是私有的、不平等分配的所有物总和,而公社不仅要以生产领域最大社会化为目标,还要以使用和消费领域为目标。和任何共同体邪教不同,“独处权”(马尔库塞)和退出私人生活是不可侵犯的。但是,公社的私人领域不同于以批量销售和有计划淘汰,主要不再是这么一个空间,稳定增加的商品堆积流必须在这个空间消化才能使系统运作。如果食堂和洗衣房在本身功能之外成为遭遇的空间,那就不再有必要在每栋公寓安排洗碗机和洗衣机。公社通过一些直接措施,就可以瞬间解决一些技术官僚永远咬紧牙关在解决的问题。公社不再延续无从遏制的“电动车”灾难——这些车和汽油车消耗一样多的劳动、资源、街道和城市空间,不会消灭尾气污染,而是带来高毒性的电池生产——而只是建一些有轨电车道(没有了汽车,也就不需要花费大量精力往地里挖隧道)。空中交通没了不断滋扰的游客和经理人也可以大幅减少,以便地球稍稍喘口气。
即便是活在世界丰裕地区的无产阶级也能从革命中获益良多。首先在1871年巴黎公社期间出现的公社奢侈品提法就值得重拾,它表明了以创造城市空间的新方式来消灭亵渎的物质生产与艺术之间的分野这种做法。公社奢侈品必须是任何新社会的主导动机。往好的看,如今为所有人存在的奢侈品就以公共图书馆的形式存在着,由于它们不盈利,就必须由国家运营。公社越发展自身的社会财富,跟踪个人消费这个问题就越能解决。[8]
7 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
一面是现状的非理性,一面是现状助长的潜力,两者让我们有了自由社会可能是什么样的梗概:将现有的机器按照生产者的需要而重建;消灭无意义的职业,必要的任务则自动化或者重新组织为有趣的任务,又或者不可行的话,轮换沉闷却必不可免的任务;消灭雇佣劳动,让获得商品的渠道不再按照自己的贡献而定;发展真正的社会形式的财富。但是这个梗概没有涉及使所有事情成为可能的社会形式。
这种形式是关键。不论目前的生产方式的毁灭与非理性性质有多明显,不论新技术呈现什么潜力,只要目前的社会形式是数十亿人唯一可以理解的共存方式,事情就不会改变。正如我们抗拒仅仅将现有的贫困的方方面面变成永久的左翼现实主义,我们也应该抗拒这样一种伪极端主义,对孤立的暴动喋喋不休,宣教最有可能的毁灭,但是对新社会的问题就只能给出个体总自由的含糊老调。这些问题要求的是社会中介的新形式,在这种形式之中,一般与特殊并不敌对,而是特殊的有意的创造。实际的社会主义虽然出于十月革命,却将带有总体主义特质的国家权力捧上王座,把马克思的“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纲领变成阴暗的对立面。这凸显了在让所有人各安其位的国家强制之外,使用其他手段来克服没有节制的资产阶级市场经济特殊主义是多么严峻的挑战。自由社会要克服这两者,就是说,一方面要以计划、合作和有意的方式塑造关键的物质过程,这些过程在今天由于竞争和危机而盲目和不幸地进行着。另一方面,要“重新收回”此前国家执行又依然必需的职能,但是又不能成为社会以外的一个强制工具。前者是后者的必要套件:只有由平等的社会控制生活的物质必需品才能够让国家,这个维系互相脱节的社会的一个外在枢纽(马克思:资本主义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成为多余。资本主义的典型特点,即经济与政治相分离,在那时候会被消灭。
从历史上说,这种描绘并不是乌托邦,而是获得了无产阶级实在实践的补充。只有在1871年巴黎公社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得出1848年夺取国家权力的纲领是过时的结论,而1905年以后反复出现的工人委员会激励出决定性的反国家共产主义。在前一种情况下,使得马克思谈到“反对国家本身、这个社会的超自然的怪胎的革命”的原因,主要是“废除常备军而用武装的人民来代替”,是普选选出的城市代表随时可以撤换的事实,还有公社不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这一点。社员起义被调整为打碎旧的集中制国家权力,以地方的“生产者的自治机关”所统治的公社网络取而代之。在后一种情况下,尤其是安东·潘涅库克(Anton Pannekoek)详细描述的工委模型之中,“工作机关”加上可以撤换的代表理念得到了延伸,但在这里严格植根于和配合生产。社会是要像地面上建金字塔一样,以工厂为决定性单元建立起来的:“政治与经济之间,并没有专家机关的生命活动与大量生产者的活动之间那样的分离……委员会不是政治家,不是政府。他们是信使,承载和交换意见、意图和工人组织的意志。”“就算是最集中的委员会也不具有政府性质”,因为“没有权力机关”。不再有国家这么一个与社会分离的集中化力量。
几十年来,工人委员会对许多极端派来说依然是东方国家社会主义之外的一个选项。“偏向工人委员会的相当坚挺的真实趋势”曾经是给予情景主义者乐观情绪的因素之一,现在依然不再。但是,具有无国家社会意味的组织形式还没有在过去几十年的斗争中出现。近期城市广场被占领是斗争手段,是出自并符合工人阶级的碎片化,但是和委员会不同,这些手段没有预示出新的社会组织。希腊、埃及和西班牙的广场占领具有前景式的自我组织,在某种程度上追随了委员会的步伐。但是,它们不仅持续脱离了生产,也就是说,脱离了资本主义关系要解体的决定性杠杆,而且除了总体的不满之外,没有具备清晰边界的实践基础。在这些广场的群众集会上,大家单纯代表自己,出于充分的理由质疑官方政治,却对自己的公民身份有更强烈的依附,结果是大家很快就感到无聊的无休止闲谈。大家只不过在草地见个面,无所不论,这很难说得上是公社的模型。
从许多角度来看,委员会这个旧构想看起来即使不过时也当然老派了。按潘涅库克1947年以来的勾勒,每个工人都安排到一个单独的工作地点,一生的焦点在生产之上,整个社会架构似乎是没有冲突的有机体。但是,如果只是将委员会理解为在某个地方生活或工作的所有人讨论共同利益攸关的事情、将讨论的结果付诸实践、并且通过随时撤换代表的手段来咨询其他委员会,那么这种形式有可能成为新公社的主心骨。也就是说,如果这种形式真的能够成型,并且持续到完全不同的形式发明出来之前。委员会、草根集会、或者别的什么称呼,它们组织的基础和互相交流的方式,会根据各地的条件而不同,当然会频频变化。按霍克海默所说,“宪制的不稳定是无阶级社会的典型特征:自由联合的形式并不凝结成系统”。
过去几十年里,这些自由联合的条件,尤其是北方世界的条件,在多个方面有相当的改善。第一,自由时间增加了。人们只有不被必然王国过度吸收以后才能够参与公共事务。第二,总体教育水平比第一批委员会出现的时候变高了。能读能写,能讲外语的人变多了,许多人有一点出国旅游的经历,也能够在雇佣劳动之外追求个人兴趣。第三,信息技术带来了全新的机会,可以在没有中央计划机关的情况下协调生产和度量需要。比起邮政服务和专员,电脑和网络可能可以更轻松地决定需要什么,而沟通好在哪一个生产节点上需要更多帮助同样更加轻松。正如人们如今以电子化方式安排“事件”,农业公社也能发出需要支援收割的信号,欢迎所有人核查自己能否出力。工厂可以协调自己的工作量,规范商品流通,交换出自经验的知识。每个节点必须有负责团队,但是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天赋而在各个职业之间广泛流动。商品不会像真社会主义的时候那样,在这里有需要的时候在那里腐烂。技术将不单促进生产和分配。对商品进行心怀生态的集体利用,这在今天只是资本主义商业的新一个分支,就是所谓共享经济,但在那时候也会更加轻松。任何人都可以追踪自己感兴趣的进程。潘涅库克期望从个体厂房解体而实现的透明度(“现在社会劳动过程的结构已经袒露在我们面前了”),在那时候将以1947年他难以想象的程度实现。再者,20 年后的情景主义者拉乌尔·瓦内格姆(Raoul Vaneigem)曾经期望,“电信技术的极大丰富”将服务于“基层的代表进行持续控制”,自那时起,这种极大丰富有相当的成长。因为社会学家一直喋喋不休“通信”“网络”“知识社会”等等花哨话,如果还如此专注这些提法不免令人羞耻。不过,这些提法确实点出了内涵,数码技术在自由社会里能给出的许多机会,同样凸显了有些人认为上述提法仅仅是工作时间的完美度量法,他们是多么眼光狭小。
如此,今天委员会或者集会将无需应付许多琐碎的任务。剩下的是那些影响广大的决策问题,不能在地方层面或者仅仅通过技术协调来处理。社员在1871年纲领所预示的去中心化在今天依然值得追求,但存在局限。比如说,某些情况下由地方生产东西是没有意义,甚至不可能的。全球公社,或者在一段时间内只涵盖广大地区的公社,会面临使用的资源有限的问题,这只能集中解决。这种公社如果以非威权主义的结构为基础,其中的中央机关知识追随“从下而上”的指令,就会很容易被任务压垮。让每个人参与每次决策,这是消极意义上的乌托邦。这种局限必须以某种方式解决,以防出现充斥着专家的政治空间。
由此可见,国家的消失并不会带来变化不定的条件,而是需要高度发展的社会自组织形式。“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要求全新的问题处理方式,处理如今由法律、刑事法庭和监狱要负责的问题。现在的多数甚至大多数罪行,比如财产罪,是物质必然性的产物,在上述条件下会自动消失,但是某些问题会继续存在。我们必须以苏联法学家帕舒卡尼斯(Evgeny Pashukanis)的批判为基础,他认为“刑法和一般法一样”,是“利己主体和孤立主体之间的某种形式的关系”,植根于资产阶级的等价原则之中。报复必须替代为改进和康复,这样“庭审案件和庭审判决将变得完全多余”。未来的社员不应该建造监狱(Emma Goldman认为这是“社会性罪行和失败”)和在眼下已经逐渐失控的法律体系那里浪费时间,而是要向解决冲突的新方法,向有助于“改善”暴力性个体的方法而努力。这可能涉及一些强制性措施。从根本上看,挑战在于保证法权关系的解体不会导致退化到比现状还差的时候,在现状的时候,法律的抽象性本身起码在理念上可以保护个体免受国家专制主义的侵害。“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不能意味着个体完全听命于邻里的喜怒无常,也不能意味着被抽象统治的资产阶级社会替代为小共同体组成的直联体。对此不存在担保。这是人类未来要面临的巨大却并非无法解决的挑战之一。[9]
8 消灭性别与家庭
这里列出的挑战会以许多方式影响性别关系,但是不一定终结这些关系带来的痛苦。这些关系从性别的劳动分工和刻板印象到针对女性的暴力不等。性别关系可能会在创造公社的阶级斗争之中发挥中心作用,女性社员也一定不断要求具体直接的变化。完全消灭既定的性别关系可能会是几代人的任务。换句话说,不会建立直接的和谐,事实上性别相关的斗争会继续加剧,正如1871、1917及其后多年、1936/37和1968年等多数现代的动荡一样。性别关系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尽管紧密纠缠,却不是同一回事。这就是如今许多女性主义者不批判资本主义也依然成立的原因,就是可能反而有男性社员不愿意舍弃性别角色,更愿意写软件而不是换婴儿尿片的原因。不过,要在这个方面超越旧世界之道,还是可以找到欣喜得多的条件的。
第一,尽管经典的父权制出现了趋势性侵蚀,但是那个推动了(不一定创造了)这种特殊的性别劳动分工的稳定性的因素,依然会随着雇佣劳动的终结而清除掉。正如我们在另一篇文本中所说的,“不论劳动市场上的女性是否确实打算生孩子,生育孩子的能力对她们来说一般是劣势;由于她们的工资偏低,她们要是一旦有了孩子就几乎一定是照料孩子的人。”如果劳动市场替代为社会任务的有意分工,就能稍微提高超越这种无政府主义的概率。一切事情归集体讨论的时候,男性要不在俗务上帮忙(比如育儿和家务),就至少不得不想一些好理由了。
第二,目前有许多分派给女性的任务可以集体处理。如此看来,下一次革命不需要有太多创意,这个理念本身就和在实践中尝试执行它一样古老。只需要回想亚历山德拉·柯伦泰(Alexandra Kollontai)就明白了,她在苏联早期提倡集体安排起居和育儿。这与资本主义甚至也不是必然悖谬:要把女性动员去进行雇佣劳动的时候,政府机构有时候会养育儿童。但是在大规模失业的情况下,世界多数地区对女性劳动的兴趣似乎相当有限,即使存在,育儿在那里也依然是私人性操劳,遗留给了祖父母和邻居处理(中国就有整个村子只有老人和儿童居住),因为这样便宜。公社从金融考量中解放出来以后,可以根据现有的需要来重塑因为没有生产力而被今天的世界忽略的东西。
第三,已婚配偶和家庭如果不作为生活方式而消失,也会作为经济单元而消失,因为那时候没有私有财富,没有银行账户,没有房地产,没有继承。物质利益与人类亲密关系的亵渎融合会被消灭。这对父母与孩子,对性别之间的关系几乎肯定会带来好处。女性不会因为再也无法获得丈夫的收入和容身之所,最终陷入贫穷就被迫克制自己的离婚愿望。除此之外,私人和社会会通过改变关系而具备全新的性质。目前对家庭所倾注的幸福希望往往落得无比的失望,这种倾注大多是对非人类的条件产生的反应。小家庭集体内部的温馨存在,则是人人都没有归家之感的社会的极端对立。如果人们在革命之后还是想生活在核子家庭里,当然没有人会计划禁止,但是这样生活的意欲将会降温,即使没有完全消失,也会引发比今天少的悲剧后果,因为那时候个体在社会内部会拥有完全不同的位置,家庭和经济功能将会结束。
从今天的性别关系混合进了雇佣劳动和家务(包括育儿)之间某种对立的程度来看,社会革命慧聪根本上推进我们从这些关系当中解放出来。不过,如此这般的进步并不存在担保。即使用理性和社会的方式安排育儿以后,也有可能只有女性育儿,由此来看,某种劳动分工之外的性别关系,它的所有方方面面不大可能自动消失。经典的性别刻板印象继续存在,但是在晚期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国家那里出现了流动。这些刻板印象之间的历史纽带,加上社会进程被切割为市场经济与私人再生产,这些都是相当明显的迹象。但是,这些迹象已经深深插入了人们内部生活的最隐秘角落,还继续成为身份的来源。要只是因为这些性别角色是在潜意识发展存活的,那要消灭这些角色就需要时间:“虽然摧毁国家权力尤其可以认作集中的‘推翻’,但是(某人自身的)性别主体性的必要转变和自我转变,几乎很难认作在文化上具有革命性的漫长过程之外的其他东西,这个过程会不时爆发,但一般来说只会在日常人际关系和新文化生产之中一点一滴地发生。”(Lux et al)[10]
9 蓄势待发的革命
向公社的过渡既不能认作征服国家权力,也不能认作声称已经蓬勃发展的新生产逻辑的逐步扩张,更不能认作这两者的联合企业,也就是左翼政府加从下而上的另类实践。马克思列宁主义对革命的理解不需要多说:政府国家权力、经济国有化以后是耐心等待国家“自行消亡”。但是如果反对这种观点,那么破裂的必然性就让位于公共品或者价值批判等头衔的另类渐进主义。这种渐进主义号称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突破成果,告别了工人阶级以后逐渐向1970年代的绿色另类意识形态靠拢,粉饰成和“商品-货币系统”相脱钩,提倡建立不同生活和生产方式的孤岛,从而逐步动摇系统。从有可能创造市场之外的生计这种程度来说,当然没有理由不这么做。但是,终结财产不仅要理解为没收控制生产资料(第一个决定性对峙)的人的财产,还要理解为终结企业之间的分离,将之消灭以后替代成社会生产流之中的节点,仅此而已。不终结财产就会事倍功半。没有革命性的群众运动,就不可能获得充分的资源开展另一种生活,即使可以获得资源,也很难长期维持与市场关系之间的独立性。
向公社的过渡只能理解为所向披靡的占领运动,将一切有用的东西没收,包括住房、公共建筑、工厂、农地、交通工具等,同时将一切必须关闭的东西阻拦或者破坏掉。关键是利用一切俘获的东西来不断扩大运动,否则会全盘失败。商品必须只能分配,医疗和交通等服务必须免费提供;不能像苏联战时共产主义一样用法令“消灭”货币,而是要令可能已经因为深重的社会危机而贬值的货币变得多余。这种实践已经出现在所有伟大起义那里,而共同的目标使得所有权这种小问题变得无关紧要。68年五月风暴的时候,农民将田里的水果带给巴黎的占领者,近年许多广场占领运动也免费派出食物,治疗伤者,必需的任务就自愿共同分担。
但是,如何夸大都几乎不为过的挑战就在于超越搜刮和分配商品,同时开始用新方式生产。工厂如何运作,在里面的工人最清楚,即使在高科技的年代,没有他们的合作就一事无成。有对这些努力感兴趣的人的支持,他们就可以直接开始按照自己的需要来调整工作流程,若有必要,也可以开始按照运动的需要来转变生产,将产品给予萌芽待发的公社。就连1936/37的西班牙社会革命,也已经面临经济上依赖没有发生起义的地区这个问题。今天这个问题更甚者,全球劳动分工会迅速扼杀任何纯局部的革命尝试。这不是说革命必须在整个世界在同一天爆发,而是说,如果革命不迅速扩散到那些仅用必需品就能扑灭革命的大型地区,一切都会失败。扩散到许多国家的深度危机可能会成为这种扩大的催化剂。
上述运动的轨迹当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当局的反应。它们是尝试在军事上歼灭起义的焦点,比如1871年流血周,还是和1989年东方的年老官僚一样疲惫退位,这最终会带来决定性意义。关键在于否定“必需品和必需服务的供应“,从而“按阶级界别来分散武装力量”,削弱军事机器(全球愤怒工人(Angry Workers of the World))。虽然有可能必须用武力保卫成果,但是革命运动最有潜力的武器就是满足人民的物质需要、在起义的过程中也能创建新的人类关系的能力。重点在于将这两个因素如此结合起来,让人民群众看到尽管风险重重,但抛弃现存的秩序突然变得不言自明了。连坦克也不能挽救工人阶级不再运作的东西。
事情的要害是这样的:在目前的状态下,今天遍布全球的生产机器无论有多少潜力,依然是起义的一个可怕的出发点。目前的状态与可能的公社之间有深深的鸿沟,这里暗示的跨越鸿沟的方法在某些方面可能显得异想天开。从政治上说,这反映在此前提到的局部化公共品和某种新无政府主义等等转向之上,这些转向认为“基础设施”是敌人,漫无目的地去拆铁路。但是这种做法同样存在于国家必不可免这个假想之中:世界已经如此复杂,没有伟大舵手的领导,就无法过渡到后资本主义社会。两个极致立场的错误轻易就能展现。第一个立场还没到再次没收的巨大挑战就毫不犹豫投降了,第二个立场高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可控制性。草拟任何一种反提议只会更加吓人。正是因为公社没有被历史的客观路径提前规定,所以今天才应该讨论未来可能是什么样的剪影。工人阶级今天越是在全球范围讨论这个,一个全然不同的世界就能越清晰地浮现眼前,新一场革命运动毕竟还能发生的机会就越大。[11]
回到本书主页
[1] 【译注:英文版为 Friends of the Classless Society, “Contours of the World Commune,” Endnotes 5 (2019)。怀谷译。作者 “无阶级社会之友” 是德国柏林的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本文德文原文首出版于他们和另外四个小组一起编的Kosmoprolet杂志第五期(2018)。】
[2] “知识的社会化已经达到如此高的程度”,约翰尼斯・阿尼奥利在1975年注意到,“现实之中的‘作者’只不过挑选和编辑集体生产的材料、信息和反思,以及集体体验的实践结果。”(《资产阶级国家的反思》(Überlegungen zum bürgerlichen Staat)引言)。我们就是从这个意义之上不去宣称任何原创性的。我们不去尝试宣布新“方法”“图式”和“理论学派”,而是利用大略两个世纪的现代阶级斗争已经生产出的思想财富。几乎所有内容都有人说过,我们只不过面临眼下的状况而用稍微不同的方式再说一次。
[3] 引文出处:德波,《景观社会》;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本雅明,“1934年7月26日给维讷·克拉夫特(Werner Kraft)的信”,The Correspondence of Walter Benjamin, 1910–1940。共产主义应该是什么,对提出这个问题所产生的普遍反对意见已经被德国的Paeris小组批驳过:“怪人、空想派、反共”(Spinner, Utopisten, Antikommunisten)Phase 2, no. 36。“法兰克福学派”的拥趸在“禁止圣像”(Bilderverbot)的问题上其实并不太迂腐。霍克海默认为,要承认决定新社会走向的人不是孤立的理论家,而只有参与实践性解放的人民,这样做“不会阻止所有接受新世界的可能性的人去考虑,人们如何在没有基因调控、惩罚部门、模范工厂和被镇压的少数派的情况下生活”(“威权主义国家”(Authoritarian State),1940)。阿多诺注意到,“禁止想象事情应该是什么样,社会主义的科学化,前者并不一定有利于后者。”(傅立叶(Charles Fourier)《关于四种运动的理论》(Quatre Mouvements)导言)。左翼对技术进步的信仰这种震惊的例子可见Paul Mason, Post-Capitalism: A Guide to our Future (2015),以及所谓“加速主义者” (Nick Srnicek / Alex Williams, Inventing the Future, 2016),他们宣传“保证基本收入”的妄想只会加速阶级意识的衰败。对Mason的摧枯拉朽的批判可见Rainer Fischbach,这位左翼凯恩斯主义者批判的理由很有趣:《美丽的乌托邦:Paul Mason,后资本主义和无限富裕的梦想》(Die schöne Utopie. Paul Mason, der Post-kapitalismus und der Traum vom grenzenlosen Überfluss) (Cologne 2017).
[4]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1875)之中提倡共产阶级二阶段论,第一阶段依然将个人消费与劳动时间相联系。这个文本同时还很有先见之明,攻击德国社民党神化了国家。今天重新拾起这个想法的人,包括提倡“劳动时间账户”的新列宁主义者Dietmar Dath(《黑暗中的阶级斗争》(Klassenkampf im Dunkeln), Hamburg 2014),反威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Peter Hudis(Marx’s Concept of the Alternative to Capitalism, Leiden 2012),科克肖特和Allin Cottrell (Towards a New Socialism, 1993),以及数不清的其他人。我们的批判大部分追随Raoul Victor的卓越贡献,见”The Economy in the Transition to a Communist Society”, Internationalist Perspective 61 (2016)。克鲁泡特金的引文出自《无政府主义》(Anarchism)(1896)。
[5] 引文出处: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尔库塞,《马克斯·韦伯著作中的工业化与资本主义》(1964).意大利工人自治主义者拉涅罗·潘齐耶里(Raniero Panzieri)追随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对机器的论述,写出了在今天依然精彩的机器批判,见“The capitalist use of machinery: Marx versus the objectivists” (1964)。批判理论框架内的重要讨论提议可见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1964),以及Hans-Dieter Bahr的《“政治技术学”批判》(Kritik der ”politischen Technologie” )Frankfurt 1970。所谓“生源形式论”(germ form theory)可以在keimform.de找到记录。新技术方面,当然包括呼吁保证收入这方面的论述,可见“混沌电脑俱乐部”(Chaos Computer Club)的两位发言人Frank Rieger和Constanze Kurz(《不工作:探索取代我们的机器》(Arbeitsfrei. Eine Entdeckungsreise zu den Maschinen, die uns ersetzen), Munich 2013)。更加批判并且考虑到目前工作状况的可见Matthias Becker, 《自动化与剥削:数码资本主义如何转变劳动?》(Automatisierung und Ausbeutung: Was wird aus der Arbeit im digitalen Kapitalismus? ), Vienna 2017)。亚马逊工人的要求有一个不错的文献,Georg Barthel / Jan Rottenbach, “数码机器时代下的实在的从属和屈服:亚马逊莱比锡罢工工人的联合考察”(“Reelle Subsumtion und Insubordination im Zeitalter der digitalen Maschinerie. Mit-Untersuchung der Streikenden bei Amazon in Leipzig” ), PROKLA 187. 对中国越来越多部署机器人的学术性研究见Yu Huang and Naubahar Sharif, “From ‘Labour Dividend’ to ‘Robot Dividend’.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Labour Power in South China” (2017)。
[6] 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 《论狗屁工作的出现与劳动价值的再思》(“On the Phenomenon of Bullshit Jobs”); Meinhard Creydt引文出处, 《论后资本主义未来的46个问题:经验、分析、提议》(46 Fragen zur nachkapitalistischen Zukunft. Erfahrungen, Analysen, Vorschläge)Münster 2016.
[7] 《关于一般化的自我管理而向文明人发出的通知》(“Notice to the Civilized Concerning Generalized Self-Management” (Internationale Situationniste 12, 1969))的一个革命场景依然值得阅读,拉乌尔·瓦内格姆(Raoul Vaneigem)在通知中稍稍含糊地认为,“行政和官僚机制、景观生产和纯商业的工业”等等,都是“寄生行业的群众机会纯粹直接地决定打压这些行业”的例子。生活在柏林这样的晚期资本主义服务业大城市,人们会好奇除了医院和公共交通,还有什么不会掉入这个范畴。关于郊区之为非处所,见德波《景观社会》第七章。关于能源生产尚未解决的问题:Rainer Fischbach, 《人-自然-新陈代谢》(Mensch–Natur–Stoffwechsel (Cologne 2016))。Fischbach表明,可再生能源被绝望地夸大了,至少为了遏制全球变暖,必须极端削减能源消费。他攻击对能源行业和工业的小规模和局部生产的绿色-另类拜物做法(只有延伸到广大地区的生产节点才能抵消可再生能源的上下波动,而标准化的大规模生产需要的能源、资源和劳动力最少;我们在第七部分提到了这点,不过有一点勉强,因为我们没有任何绿色-另类倾向,不过似乎去中心化依然有一定优势)。
[8] 阿多诺的“论需要”(Theses on Needs)(1942)在四页半的边幅里构成了一个革命日程。关于“独处权”,见马尔库塞《论反叛、无政府主义和独处》(Über Revolte, Anarchismus und Einsamkeit)(Zurich 1969)。关于公社奢侈品,见Kristin Ross, Communal Luxury: The Political Imaginary of the Paris Commune (New York 2015)。Ross揭示了巴黎公社具有巨大的实在性的一面:脑力和体力劳动的分离、等级制度下的性别关系、艺术之为奢侈品与日常生活分离、国家与民族,这些在1871年实际上已经面临挑战。如果我们在这个文本使用“公社”比“共产主义”还要多,那不仅因为“共产主义”已经被20世纪国家社会主义政权史无可挽回地污染了(这些政权不光参与集体屠杀),还是为了表明从1871年的前工业巴黎到当代的高科技资本主义,存在一条隐藏的线索。
[9]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安东·潘涅库克(Anton Pannekoek),《工人委员会》(Worker’s Council)。有一个意外的好文献是Alex Demirovic,“委员会民主或政治的终结”(Rätedemokratie oder das Ende der Politik)(PROKLA 155),专门质疑了潘涅库克所预示的政治被经济完全吸收的情形。关于法律的批判:帕舒卡尼斯(Evgeny Pashukanis),《法的一般理论与马克思主义》(1924)。关于监狱:Emma Goldman, ”Prisons: A Social Crime and Failure”, in Anarchism and Other Essays (Stilwell 2008)
[10] Kat Lux / Johannes Hauer / Marco Bonavena的引文出处, “分歧的视角:关于未来冲突中的性别关系的思考”(“Der halbierte Blick. Gedanken zum Geschlechterverhältnis im Kommenden Aufprall” ), diskus 216 (2017).
[11] 价值批判的拥趸关于如何超越资本主义的关键文本,依然来自Robert Kurz, “Anti-economics and anti-politics”, 出版于krisis no. 19/1997。Kurz对演进式变革的局限依然只有模糊的想法,而当代的拥趸则将“希腊极左翼联盟和西班牙‘我们能’党等等毕竟出于社会抗议运动、具有真正重要功能的党派”赋予了超越商品社会的能力(Norbert Trenkle,《危机中的社会解放》(Gesellschaftliche Emanzipation in der Krise),2015)。全球愤怒工人(Angry Workers of the World)(伦敦)的“起义与生产”(“Insurrection and Production” )(2016)应该获得广泛讨论。他们将英伦三岛用作例子,以少见的具体角度反思在今天如何展开无产阶级革命。我们希望他们的9小时工作制提议能局限在这个过程非常早期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