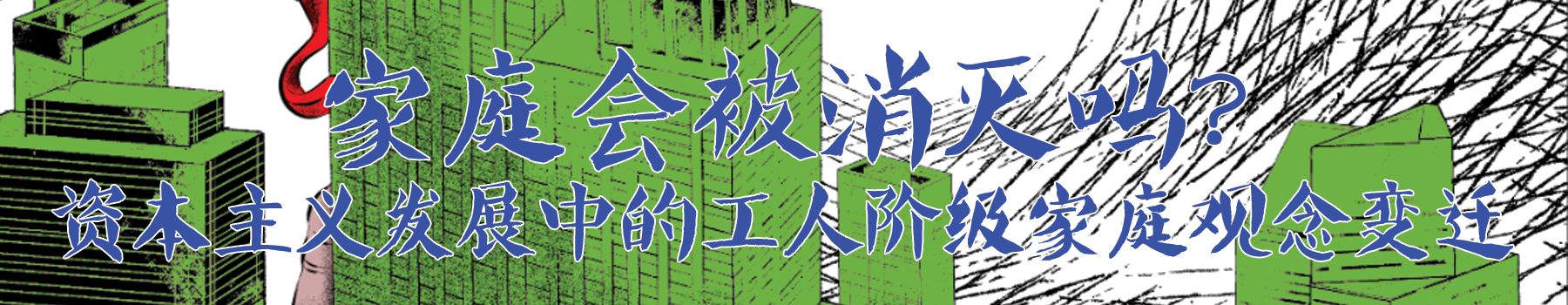
家庭会被消灭吗?
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工人阶级家庭观念变迁[1]
ME·奥布莱恩 著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消灭家庭!连极端的激进派也对共产党人的这种可耻的意图表示愤慨”。[2]消灭家庭的呼声自那时起就一直萦绕着无产阶级斗争,为不断被其他策略和战术导向推迟和取代的性别解放和性解放提供了一种视野。消灭家庭的说法呼唤对日常生活的彻底、几乎不可思议的改变。对有些人来说,家庭是没完没了的恐怖,人必须逃离家庭才能找到自己的形象。对另一些人来说,家庭是抵御市场与工作的残酷性、种族主义警察和把人驱逐出境的官员的支持与关怀的唯一来源。对大多数人来说,家庭同时具有这两方面。没有人能独自在这世界上存活;一个人对自己家庭的个人态度,直接影响到他如何理解消灭家庭的号召。
不知道一个家庭(a family)是什么样,或者或不知道家庭本身(the family)究竟是什么,使消灭家庭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一问题变得更复杂。对马克思来说,任务是要消灭教会、国家、家庭(格外突出的三件套秩序集团),并最终消灭冷漠的市场规则。马克思和恩格斯用的消灭一词是aufhebung,它经常被翻译为“扬弃”,因为它同时有保存和破坏的含义。消灭不等于破坏。在消灭家庭的运动中,被取代和被保留的分别是什么?
与其把家庭当做一系列静态的标本盒,从句法上分析它的不同定义,我认为在消灭家庭的口号的转变的背后,有一段历史性逻辑的不断展开,它可以同资本本身的动态关系联系起来。激进人士所说的“家庭”也具有一个不断演变的模式。伴随着工人运动的兴衰——它与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独特阶段及其共产主义的超越性视野相对应——家庭也存在一个连贯的分期。资本主义历史上工人阶级家庭的动态关系不断变化,可以解释革命派对家庭的批判的不断变化,最终也能说明性别自由的前景的转变。
家庭承载着在短促、异化的社会中生存的矛盾,它是安慰和绝望的来源。如今,消灭家庭的口号已经成为对酷儿爱情普遍化(从而摧毁规范性制度)的号召,以及朝向所有人的性别及性自由。家庭的消灭或许会体现为共产主义下真正的人类共同体中人性关怀的普遍化。
|
|
1830—1880年代 |
1890—1950年代 |
1960—1970年代初 |
1970年代至今 |
|
主流的家庭形式 |
资产阶级家庭 |
工人阶级、男性养家糊口的家庭形式,因工人运动得以可能 |
工人阶级、男性养家糊口的家庭形式延续 |
家庭结构多样化,但核心家庭依然存在 |
|
资本主义对工人阶级家庭生活的侵蚀 |
工人阶级社会再生产的危机;农民和手工业者家庭遭工业化侵蚀;性工作激增;奴隶制下的生而异化(natal alienation) |
一战和二战的战时动员 |
女性的白领工作机会增加 |
工人阶级、男性养家糊口的家庭形式不再可能 |
|
共产主义者对消灭家庭的设想 |
在反资产阶级社会的战争中摧毁资产阶级家庭,终结虚伪的单偶制(恩格斯、傅立叶、大多数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 |
把无工资的再生产劳动集体化,让工人阶级妇女参与雇佣劳动,将她们从强制性的家庭中解放出来(柯伦泰) |
激进女权主义者、酷儿和黑人女性试图消灭平常的封闭家庭单位,朝性解放和性别解放迈进 |
|
1. 欧洲的工业化与美洲种植园
再生产危机,1840-1880年代
1842年,一名22岁的德国资产阶级青年来到了曼彻斯特繁荣的工业中心。他在那里待了两年,试图理解英国的新城市无产阶级的生活。他把英国看做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未来,这个资本主义世界正在德国新工业中心形成,不久将遍及整个欧洲。他与人交流、读报告、在街上漫步。他试图表达他对无产阶级境况的恐惧:
到处是一堆堆的垃圾和煤灰,从门口倒出来的污水就积存在臭水洼里。住在这里的是穷人中最穷的人,是工资最低的工人,掺杂着小偷、骗子和娼妓制度的牺牲者。其中大多数是爱尔兰人或爱尔兰人的后代,甚至那些还没有被卷入他们周围的那个道德堕落的漩涡里面的人,也一天天地堕落,一天天地丧失了力量去抵抗贫穷、肮脏和恶劣的环境所给予他们的足以使德行败坏的影响。[3]
他意识到,工人阶级无法在这种条件下生存:“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最贫穷的阶级怎么能够健康和长寿呢?在这种情况下,除了过高的死亡率,除了不断发生的流行病,除了工人的体质注定越来越衰弱,还能指望些什么呢?”19世纪中叶的英国工人阶级死亡速度太快,无法迭代。恩格斯记录的状况(疾病、过度拥挤、工作场所事故、饥饿、儿童死亡)使得无产者无法把他们的孩子抚养成人。只是由于被剥夺了土地的农民不断涌入,人口才保持增长。统治阶级的评论员、早期社会工作者和社会主义倡导者统统都谴责了工业工人阶级面临的状况,他们觉察到了社会再生产的危机。
今天的研究证实了他们的恐惧[4]——婴儿死亡率高得惊人,工人阶级的预期寿命随着城市化急剧下降。对于包括非熟练和半熟练的体力劳动者在内的约一半的工人阶级来说,工资仅够维持日常再生产开支,而不够他们的代际更替。[5]
19世纪初,工作的两次重大变化造成了恩格斯观察到的情况:工厂的发展引来儿童、未婚女性和男性外出工作;已婚妇女则在家从事有偿的转包制造工作。整个19世纪,工业化国家的工厂迅速发展。19世纪初期,许多工业部门(如1816年的英国棉产业)中超过一半的制造业工人是不到青春期的孩子。直到19世纪40年代,依然有15%的法国纺织工人还没到青春期。[6]英国和法国的大多数受雇儿童是通过工人阶级男性转包的、跨代工厂劳动团队被雇佣的。儿童往往由男性家庭成员或朋友管理,在松散、扩大的家庭关系中,儿童受到男性暴力的规训,但管理者的权威有限。
结婚后,几乎所有的女性都会立即离开工厂的工作,不再回去。在欧洲和美国都几乎没有年轻母亲外出工作。[7]美国白人女性一结婚就会离开工厂,而不是等到第一个孩子出生。[8]1890年,白人女性结婚后的劳动参与率从38.4%下降至2.5%。相反,女性会在家里从事有工资工作,管理寄宿者,干“外包活”,或在家里从事“包出(putting-out)”生产:
资本除了把工厂工人、手工工场工人和手工业工人大规模地集中在一起,并直接指挥他们,它还通过许多无形的线调动着另一支居住在大城市和散居在农村的家庭工人大军。[9]
马克思描述了这种外包工作的性别化结构:“花边整理当做一种家庭劳动,或者是在所谓‘老板娘家’进行的,或者是在妇女家里由她自己或同她的子女一道进行的。”[10]
恩格斯担心城市的贫困正在扭曲无产者的性别和性。《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潜藏着各种没有说出口的性恐惧。他反复提到卖淫——道德堕落和性腐化的症状。他也暗示了住房过度拥挤的条件下的乱伦和同性恋的威胁。这种堕落并不仅限于从工人阶级整体中分流出来的流氓无产阶级,而是整个阶级范围的危机。他那个时代的社会改革家普遍认为,工人阶级若是接受资产阶级的道德主义,包括采取更接近资产阶级家庭的家庭样貌,将为恶劣的健康状况提供必要的解药。马克思和恩格斯则拒绝了这种解决方案,因为它未能触及工业雇佣这一根本原因,且资产阶级道德主义总是一种骗局。社会主义、推翻资产阶级才是唯一的出路。
总的来说,这些动态关系意味着可识别的、作为社会再生产的明确单位的工人阶级家庭的解体。工人阶级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亲属关系网络来获得工作和住房,分享资源,或决定移民。但是无产者之间的亲属关系已经不再是一种现成的、自然化的义务、关怀和支配系统。
家庭暴力
暴力和互爱在各种家庭形式中交织在一起。所有人的生存都依赖于关怀、爱、情感、性和物质资源共享的关系。阶级社会迫使这些关系采取各种特定的历史形式。资本主义的市场依赖逻辑和普遍的无产阶级化,迫使这些爱的关系呈现一种半强迫、半选择的人际依赖的特殊结构。就业不稳定的工人要依靠家庭成员和亲属来度过定期失业;同样,儿童和那些失去工作能力的人往往要依赖他们和某个有工资的人的个人关系存活。此外,自由的雇佣工人通常要靠基于亲属关系的社会网络找工作,这些网络会提供信息和支持,以帮助人找到并保住工作。这些关系可能是真正关怀的来源,但不可避免的依赖关系使它们常常受到暴力、虐待和支配的威胁。对于一切形式的性别暴力来说,威胁或许就隐含在促使施暴的社会机构的结构中。个别的家庭实际上可能并不暴力,或者不常出现暴力,但家庭作为普遍存在的机构依然可以系统地促成并准许暴力和虐待。关怀和暴力支配的结合,是阶级社会中一切家庭结构共有的双重特性。
在欧洲农民社会中,男性支配和性别暴力体现为不同于后来的版本的特殊形式。农民家庭中性别分工程度相对较低,男女都从事各种形式的家务、农场和工作。一户人家往往有多代人,或者是大家族,人们不通过家庭的土地就没有什么别的生存方式。男性是一家之主,占有妻子、孩子和他们的劳动。他们可以选择通过对妻子和孩子的暴力来行使他们作为户主的权力。反过来,男性农民和他们的家庭又屈从于封建领主的暴力。领主和封建国家依赖暴力,这是它们的阶级统治和经济剥削的主要特征。封建制下由父亲支配的家庭与整个社会的阶级结构类似,其权力的基础也是暴力。资本主义发展在剥夺农民土地的时候所腐蚀的正是这种农民家庭,而资产阶级社会所改造的也正是对应的贵族家庭。
随着农民的无产阶级化,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支配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在工业化的混乱的无产阶级化之中,暴力的作用变得更加多样了。领队的男性工人会用暴力规训在他们手下工作的妇女和儿童,男性又可以用暴力支配和他们一起生活的各个家庭成员。性工作者和其他非正式工作者会遭受顾客和警察的暴力。所有无产者都遭受来自雇主的暴力,以及来自负责社会控制、工人规训的国家代理人的暴力。
然而与封建制度不同的是,暴力不再是资本主义雇佣劳动下的积累财富的必要手段。暴力仍然渗透在英国无产者的生活中,比如那些反流浪者和穷人的残暴法律。但是一旦失去土地的农民的起义被压制,他们不再有别的方法养活自己,“自由”的雇佣劳动者就开始找工作。封建领主需要私人军队才能每年向农民征收,而资本主义雇主则可以越来越多地不再使用武力。暴力逐渐从工作场所中分离出来,转而集中在国家代理人手中——警察、国家军队——或者在家庭中私下存在。
当然,直接的暴力在另一种资本主义劳动制度下,也就是新大陆的奴隶制中是更关键的。[11]在南美的奴隶种植园,出现了一种新的劳动力代际再生产的资本主义制度,它省去了一切把生育纽带自然化的借口。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Davis)这样描述了奴隶制下碎片化的家庭生活:“母亲和父亲被残忍地分开;孩子一旦到了一定年龄,就被打上烙印,通常会和母亲分开……住在一个屋檐下的人通常是没有血缘关系的。”[12]
一旦奴隶有了孩子,奴隶主的财富就扩大了。这暗含着作为资本积累和工作过程核心的代际再生产的动态关系。大多数奴隶都不能有效地主张任何形式的父母权利,奴隶出售往往会把家庭拆散,造成所谓的“生而异化”。在美洲,被奴役者中的父亲的权力会受到严格限制,正如杜波依斯(W.E.B. Du Bois)所写的,“他的家庭、妻子和孩子可以被合法、绝对地从他手中夺走。”[13]戴维斯同样指出:“除了女性作为家庭照料者的角色以外,男性至上主义的结构不能深嵌入奴隶制度的内部运作中……因此,黑人妇女彻底加入了生产。”[14]相比之下,美国白人妇女仍被看做是属于保护性的家庭范围。无论一个北方家庭有多贫穷、绝望,白人农场的妻子都很少出来收割庄稼。
19世纪,资本主义用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摧毁了工人阶级家庭。在大西洋的这一边,英国无产者的血缘纽带正因工厂劳动的贫困化、城市过度拥挤和工业资本主义而破裂。大西洋的另一边,种植园农业把被奴役的黑人工人的代际再生产商品化,使他们生而异化。受奴役无产者和受雇佣的无产者的亲属关系对精英来说是不可理解的,也很难被法律承认,很难符合精英的社会期望。在这两种情况下,无产阶级的反常都被看做是与有产阶级的性别与性规范的巩固相对立的,后者在财产继承和地位的基础上形成了结构鲜明的家庭。消灭家庭的要求也是摧毁资产阶级社会的呼唤,虽然它没有参与进与美国南部奴隶主农业精英的对抗,但也间接和它相关,因为消灭家庭是与英国资产阶级的斗争。被奴役的工人和有工资工人之间的差异很大,种族的鸿沟分裂了世界无产阶级运动。但尽管有差异,英美两个地方资本主义都已经摧毁了工人阶级家庭。在这两个地方,消灭家庭的号召都显然是攻击资产阶级社会——美国南方的种植园精英和英国的工厂主——的一种手段。
摧毁资产阶级社会
人们可以把消灭家庭的共产主义运动,与资本主义积累的碎片化对无产阶级家庭的破坏区分开,前者是积极的取代,后者是消极的侵蚀。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已经把无产阶级家庭摧毁了:
现代的、资产阶级的家庭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呢?是建立在资本上面,建立在私人发财上面的。这种家庭只是在资产阶级那里才以充分发展的形式存在着,而无产者的被迫独居和公开的卖淫则是它的补充。[15]
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把工人阶级家庭中男性的主导理论化,而这正是后来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的一个主要关注点,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工业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阶级家庭是不可能的。
要求消灭家庭是向资产阶级社会开战的一部分。资产阶级社会秩序依赖于教会、国家和家庭,而对它们的三重消灭是共产主义自由的必要条件。恩格斯明确了资产阶级家庭的主要特征:只强加于妇女的虚伪的单偶制,把妇女看做被动的财产的性别不平等,在浪漫爱情的幌子下以金钱利益为谈判的动机,父系财产继承,还有以积累家庭财富为导向的养育。
消灭家庭的要求在《共产党宣言》中的“废除继承权”中得到了最清晰的表达。[16]资产阶级家庭是一种管理资本家财产的转移和持续的手段。资产阶级父亲把单偶制强加给妻子,以确保他们的孩子是自己的,并维持继承有序。对遗产的承诺和财产的赠与,是资产阶级父母对子女进行终身控制、在子女身上再生产他们的阶级身份、巩固自己的阶级地位的手段。家庭是由财产联系在一起的,它本身也表现为一种财产。孩子属于父母,正如妻子属于丈夫。恩格斯设想,摆脱继承将会剥夺家庭的物质基础,是消灭家庭的核心机制。
恩格斯进一步指出,摧毁资产阶级家庭和资本主义社会秩序将为真爱、完全基于“相互爱慕”的婚姻提供基础。[17]随着财产和物质的生存问题被从亲密关系中移除出去,人类可以发现他们自然和内在的性。共产主义下的性将只由未来的公民自己决定:
这样的人们一经出现,对于今日人们认为他们应该做的一切,他们都将不去理会,他们自己将做出他们自己的实践,并且造成他们的与此相适应的关于个人实践的社会舆论——如此而已。[18]
这里对解放的号召是明确,但同时恩格斯也提出了一些更有问题的主张。消灭财产和资产阶级家庭将使人类自由地追求其内在的性倾向,未来的人将自由地选择单偶制的家庭形式:“卖淫将要消失,而专偶制不仅不会灭亡,而且最后对于男子也将成为现实。”[19]婚姻将在共产主义爱情中真正实现:“既然性爱按其本性来说就是排他的——虽然这种排他性今日只是在妇女身上无例外地得到实现——,那么,以性爱为基础的婚姻,按其本性来说就是个体婚姻。”[20]
从财产的暴政中解放出来之后,人类也将从资本主义卖淫的性过度中解放出来。这种观点离后来的社会主义者过激的性保守主义只有几步之遥,后者认为性别偏异(gender deviancy)和同性恋都是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变态。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也对新生的同性恋权利运动表示蔑视和嘲弄,他们的书信里含有大量对他们同时代人的反同性恋的污蔑的说法。尽管他们都关心妇女解放以及虚伪的资产阶级单偶制的残酷性,恩格斯却无法想象也许在社会主义下,资产阶级的性规范并不会作为自然的人类条件重新出现。摧毁资产阶级家庭、神圣家庭和世俗家庭,或许会产生一些并不那么像异性恋的单偶制家庭单位的东西。
酷儿的附注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恐同”也显出一些模糊性。在1869年的一封信中,恩格斯对马克思提到了同性恋激进人士卡尔·乌尔里希(Karl Ulrich)的一本书:
这是极端违反自然的暴露。好男色的人们开始计算自己的队伍,认为他们正在国内形成一种势力……他们的胜利是必不可免的。“向前面宣战,给后面和平”!——这将是现在的联络暗语。幸好,我们本人已经老了,不怕在这个党取得胜利后强迫我们把身体献给胜利者作贡品……我们这些对女人怀着幼稚的倾爱而习惯于从前面活动的可怜人,那时可就相当糟糕了。[21]
这里表达的鄙夷是明显的,但也可看出他们自己对于落后于即将来临的酷儿革命的自嘲,反思着他们对自己的落后的忽视。[22]我要花一点时间来描述这种担惊受怕的幻想,以及在工人运动兴起之前19世纪酷儿的可能性的其他路径。
尽管卡尔·乌尔里希没想过要号召酷儿专政,但马克思很可能在夏尔·傅立叶(Charles Fourier)的书中读到过这样一种性乌托邦。马克思仔细阅读了傅立叶。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赞同地引用傅立叶的一段话:“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标准。”[23]但他对傅立叶捍卫性自由的主张似乎就不那么赞同了。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嘲笑了资产阶级对于消灭财产将导致“女性自由共同体”的恐惧,他们指出恐惧隐含的逻辑是资产阶级认为女性是财产。但他们也含蓄地拒绝了傅立叶乌托邦社会主义政治中对自由恋爱、开放关系和性愉悦的强调。
夏尔·傅立叶提出了一种社会主义的愿景,其中,爱欲和欲望是社会变革、社会凝聚力和人类实现的机制。傅立叶对资产阶级家庭做出了有力的批判,认为永久且不可逆的婚姻单偶制是痛苦、社会混乱和绝望的根本原因:“对于把沉闷、贿赂和背叛引入爱与愉悦的关系来说,难道人们还发明过比孤立的家庭和永久的婚姻更有效的东西吗?”[24]相反,傅立叶提出了一个基于“激情吸引理论”的理性社会,对人类欲望和人格类型的仔细研究,以平衡愉悦的来源并创造一个和谐的乌托邦。
傅立叶不那么有名的另一个观点是,他提出了“一个新的情爱世界”,其中爱欲是新秩序的核心。社会的结构不仅要满足所有人基本物质生活水平的“社会最低标准”,也要满足“性的最低标准”,即为每个人的性需求提供社会保障,以便为真正的、非操控性的爱提供基础:
当一个女人所有的性需求都得到满足,当她能得到所有渴望的肉体情人、狂欢和迷狂(既有简单的也有复合的),那么她的灵魂便会有足够的用于情感幻想的空间。这样,她便会寻求纯净的情感关系来平衡她的身体快乐。[25]
傅立叶想象设想了一种完全基于性无私的贵族娱乐,他们给在性上被忽略的人带来有技巧的愉悦。他描绘了这样一幅画面:一队爱的给予者在新十字军东征中穿越大陆,到访社会主义城市,参与情爱之战。他们让两厢情愿的囚徒乞求精心准备的爱欲惩罚,这些惩罚是用以展示捕获者的高超技巧的。最终这些勇敢的性冒险者会在频繁的群交中开始他们的成年生活。
这种对公开的爱欲自由社会的激情号召,也体现了傅立叶的作品更为人知的一面:号召建立起有意设计、精心组织的集体住房安排,让居民们在这里共同工作和娱乐。白天,人们一起从事专业的集体生产制作,用共同劳动和协作来提高生产率。他们也一起分担再生产的劳动,吃大锅饭。晚上则共享群交的愉悦以及其他性的连结。傅立叶很有说服力地提出了一种社会主义愿景,把集体生活、共同分担再生产劳动和自由恋爱联系在一起。他的首批追随者在1830年代的欧洲和美国建立了许多公社。整个19和20世纪,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反文化运动的公社也再次体现了傅立叶的设想的关键特征。
傅立叶被恩格斯指责为空想社会主义,认为他对无产阶级这一能动者(agent)追求并实现社会主义缺乏理解。马克思主义运动很快便会得出结论说,产业工人是这一转变中的核心人物。但恩格斯在曼彻斯特的那些年间观察到的,并不是一个由工厂生活规训的统一、同质的无产阶级群众,而是犯罪和社会混乱的刺耳声音。由无产阶级的“性偏异”激增所激发的共产主义能动性(agency),体现的与其说是恩格斯对自然的单偶制的倾向,不如说是傅立叶的酷儿共产主义。
资产阶级对手把性和性别偏异理解为对公共秩序、资产阶级家庭的稳定性和工作日纪律的威胁。迅速的城市化和无产阶级化产生了大量集中的无产者群体。这些人见识到了社会习俗的颠覆以及对农民生活的控制,他们没有投身于资产阶级的习俗中。他们在力所能及的时间内工作,在通常施行性别隔离的行业寻找工作;在季节性周期与繁荣和萧条循环中长时间地努力干活。工作之外的时间则完全是他们自己的——这种状况是从未有过的。克里斯·奇蒂(Chris Chitty)描述了在繁荣城市的港口和街道上的大量同性恋情色的机会:
大多数男性不规律的工作和极低的工资,使他们成为嫌恶家庭责任的游牧人口……同性恋往往隐藏在更广泛的无产阶级性无政府状态的背景中……因此各种恶习委员会都打击同性恋和卖淫,因为两者都可能威胁到婚姻单位。[26]
在城市生活特有的公共隐私下,同志性爱(gay sex)扩展开来,有时是在无产者之间,以乐趣和愉悦为目的;有时是在资产阶级和无产者之间,作为紧张、越轨(transgressive)的货币交易;有时是在资产阶级之间,在寄宿公寓和起居室等私人空间里。
在工业化城市的卖淫和性亚文化中,人们捕捉到了新形式的性别越轨。一系列和变装有关的词汇出现了,此时除了顺性别的性工作者,新的跨性别女性、性别偏异者也出现在伦敦、阿姆斯特丹和巴黎的街上:Mollies(【译注】指女性化的gay),Mary-Anns(【译注】异装癖),他-她女士(he-she ladies),皇后(queens)。他们在街上向资产阶级出售性服务,躲避警察,参加骚乱,定期举办变装舞会,并在遍布伦敦的约2000家专门提供男性性服务的妓院里工作。 [27]
大量无产阶级女性也开始卖淫,顾客既有资产阶级也有无产阶级的男性。反性工作者的英国《传染病法案》的出台以及要求废除这些法案的运动,留下了大量关于性工作者生活的档案,展现了无产阶级女性在工厂劳动和性工作之间的流动性。性工作能带来比制造业更高的报酬,许多无产阶级女性都时不时地卖淫,同时也与家庭和邻里维持着积极的强纽带。[28]《传染病法案》恰恰是切断这些纽带、孤立性工作者,把她们当做偏异者、与体面的工人阶级区分开的生命政治的运动的一部分。
美国刚刚获得解放的奴隶也带来了新的家庭愿景。黑人无产者运用他们在奴隶制时形成的多样浪漫关系规范,把握他们建立新家庭和性关系的自由。在美国内战后收集的关于黑人家庭的政府记录中,历史学家发现他们的人际关系与家庭结构比同时代农场或工厂中的白人更加多样化。重建运动(Reconstruction)时的许多黑人情侣都以“情人”或者“试婚”的关系“交往”,或者以非婚姻的、暂时且往往是非单偶制的浪漫关系“同居”。在这些暂时的关系中,情侣也会共同抚养“情人小孩”。[29]这种情况(尽管称呼不同)对今天的美国人来说可能很熟悉,但在1870年的白人家庭中却很少见。政府代理人、传教士、警察和新兴的体面黑人都试图粗暴干预这种非正式的结合。黑人情侣被要求接受一系列联邦和教会服务并合法结婚,不久就有黑人因违反婚姻法而被调查和起诉。
对19世纪工人阶级生活中日益扩大的性偏异和家庭异质性的认识,指向了另一种性别政治,它与社会主义运动在根本上追求的不同。试图在合法婚姻狭隘的体面性之外共同生活的黑人家庭、朝去剧院的人群起哄的异装的跨性别女性、在小巷里做爱的水手和工厂工人,以及巴黎公社中开救护车的妓女,都指出了摆脱工人阶级社会再生产危机的另一条道路。此时工人阶级家庭的消灭没有带来家庭的自然化再记认(reinscription)[30],也没有那种即将成为社会主义运动主流的性别保守主义。这些无产阶级性偏异者指向一种不同类型的酷儿共产主义,而这种共产主义在随后几十年的工人运动中却消失了。
2.工人运动与男性养家糊口的家庭
马克思和恩格斯谈到单偶制的核心家庭时,指的只是资产阶级社会,而新兴的工人运动开始把提高家庭工资作为核心要求,由此确保了实现体面的工人阶级家庭生活所需的底线。从1880年代持续到1970年代中期的工人运动塑造了一种肯定性的工人阶级身份,作为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会中规模庞大且稳定的政治组织的基础。[31]无论是在争取工人阶级选举权的斗争中,还是在对社会主义国家和由工人阶级统治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想象中,工人的身份都为统治权和能力的主张提供了共同的基础。参与工人运动的无产阶级没有争取消灭自己,而是试图实现一个从工业雇佣劳动推导出来的世界。这些要素是包括大众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在内的各个潮流直至1960年代末起义前的共同视野。
工人运动典型的家庭理想,是一个男性挣钱供养一个没有工资的家庭主妇、供养孩子上学,而他们的家庭是体面的道德与性规范的核心。在一定程度上,工人运动就是为了这种家庭形式而奋斗的,并且在运动的上升期一度成功了。这种男性养家糊口的家庭形式,加上与之相伴的工人运动的经济及政治胜利,为工人阶级的代际社会再生产的维持创造了相对稳定的新条件。即使对于在经济上做不到把妻子或母亲完全排除在劳动力市场之外的工人阶级家庭,这种家庭形式以下一些关键要素对于新产生的工人阶级的体面性来说,也变得至关重要(而这在以前的时代是罕见的):不与其他家庭生活在一起;尽可能争取单户住宅;男性控制家庭财务;在孤立的家庭结构和住所中,父亲对家庭成员的身体和性虐待不再受到邻居的监视;妻子则承担着无工资再生产劳动的全部责任。
这种家庭形式的巨大胜利,体现为它提高了数百万工人阶级民众的生活和生存水平,并为稳定的邻里组织、持续的社会主义斗争和重大政治胜利奠定了基础。这也是工人运动把自己区别于流氓无产阶级、黑人工人和酷儿的手段。这种家庭形式将为美国白人身份和中产阶级财产所有权提供性和性别基础。在这里,我们可以这种家庭形式称为“男性养家糊口(male-breadwinner)型”或者“家庭主妇型(housewife-based)”,表明这种家庭形式对男性化的有工资劳动和女性化的无工资劳动的二重依赖。由于工资之为枢轴对于该形式的维持至关重要,也可以把它简称为“家庭工资”形式。
在1880至1890年代间的欧洲工业中心,多个因素共同为男性养家糊口的范式创造了条件。[32]在对混乱的工人阶级叛乱的恐惧下,工会、工人党派以及自由资产阶级的社会改革,赢来了一系列规章、举措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极大改善了工人阶级的生活,也给男性养家糊口的范式出现作出了贡献。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发展推动的结构变革巩固了工厂的有工资生产,把儿童和已婚妇女从有工资劳动大军中驱逐出去,并降低了消费品的成本。
工会的鼓动和组织赢来了工资的显著增长以及工资份额的增长,生活水平得以全面提高。更高的工资使得只依靠一份工资生活的家庭成为可能,这把体面的工人阶级与流氓无产阶级区分开来。男性养家糊口的家庭这一愿景给工人、雇主和国家提供了象征性的团结。1890年代,工会明确地把“家庭工资”的诉求作为提高工资的合法基础。这一号召也引起了他们进步的资产阶级盟友的共鸣,原因恰恰是这体现了工人阶级怀有资产阶级的愿景。在男性工资较高的同时,工会也组织起来把女性排除在他们的行业之外,作为防止竞争和工资下降的一种手段。他们在1880、90年代间成功把妇女排除了。男性工人阻止女性就业有着合理的理由:在工会没能阻止女性就业的地方,工资会由于劳动力供应增加和女性的工资较低而大幅下降。工人阶级男性比女性有更好的就业机会,这反过来又使工人阶级家庭有更合理的理由把精力集中在最大限度地提高成年男性家庭成员的有工资工作上。[33]
除了上述争取提高工资的政治进展,资本主义竞争也压低了消费品的价值,从而提高了实际工资,进一步改善了整个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以及之后一个世纪的资本主义发展期间,工人阶级消费品的生产率的提高改善了很多工人阶级人口的生活水平。
此外,当雇主开始试图更全面地控制工作流程、取消工作团队,他们也大幅减少了对儿童的雇佣。基于团队的工作模式的结束,逐渐与限制童工和儿童工时的政治运动重合。离开了工厂的孩子们进入了新的义务性公立学校系统,学校又进一步向他们灌输资产阶级家庭理想。
制造商逐渐把生产从家庭转移出去,整合进工厂中,这结束了能让母亲在家从事有偿劳动的外包系统。适合母亲的有偿工作消失后,母亲越来越多地在家中从事无偿的再生产劳动。只有在分娩前或孩子长大以后,妇女才能从事有偿工作。工厂和家庭之间的这种日益扩大的分工,巩固并加强了一种关于工作的特殊的性别化的、主观的理解:有工资劳动男性化与无工资的再生产劳动的女性化。长期以来,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都很关心妇女工作的侵蚀效应,这体现出一种关于家庭生活该如何正确组织的观念。随着1890年代资本主义发展和政治权力的种种变化,工人阶级的其中一个阶层实现了这种家庭形式,以及与之相伴的性别分工。
在社会主义组织行动的推动下,市政府为这些新的体面的工人阶级社区建设了基础设施:自来水和污水系统、安全的住房和作为公共交通工具的有轨电车。这些基础设施极大地降低了疾病和死亡率,使工人阶级能在更远离工厂、更舒适的条件下生活,形成更严格的个人卫生习惯,这也进一步把他们与穷人区分开来。
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允许、激励并迫使工人阶级家庭采取男性养家糊口的形式,这为一种肯定性的工人阶级身份提供了性与性别的基础。在1873至1914年的欧洲各层次工人阶级家庭预算中,一名成年男性提供的收入份额显著增加,通常稳定在70%至80%左右。男性养家糊口的范式的巩固时期似乎表现为已婚妇女经济活动的一个U形低谷——在1910年至1920年间达到最低值。[34]
这种家庭形式为工人运动赢得的体面性是不可低估的。工人阶级经常被描述为生物学意义上的亚人,智力和文化能力在根本上低下,完全不适合参与任何形式的治理。这种对工人阶级的敌意与种族征服和意识形态混在了一起,固有的基因劣势这种观念被当做反对黑人、移民、犹太或爱尔兰工人的武器。对于工人运动来说,在一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成员眼中赢得体面,以及在他们自己心目中的尊严,这对于一场更广泛、最终有效的斗争来说是关键和必要的一环——包括取得投票权和参政权,使工会活动合法化,让工人阶级生活的许多方面非罪化,以及大幅提高人的生活水平,降低婴儿的长期死亡率。对许多人来说,这种体面是走向充分社会主义和充分解放的长期革命斗争中的一步。在今天,“体面”往往意味着政治保守;但对于参与工人运动的许多人来说,这曾经是一种获得实质权力的手段,也是社会主义对社会的一种革命性改造。
这种家庭形式是一种“范式”,部分原因在于它是体面性的衡量和标志。母亲继续在家中或家外从事有偿工作的话,这个家庭会面临邻居的谴责,以及越来越被社会排斥。与此同时,男性工人开始把他们养家糊口的能力与父权制的自豪感、成就感和自尊联系起来。工人们追求这种家庭结构,以便宣称他们的工资的道德维度,让资产阶级政治家通过倾向于工人的法规。家庭主妇成为工人阶级社区和社会组织的主要组织者。赋予这种家庭结构以道德合法性,也是工人运动得以将其影响力从工作场所扩展到整个社会的一种手段。
几乎没有证据能表明男性养家糊口的家庭形式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没有证据表明它是由雇主在19世纪末设计和实施的。大多数雇主对工人的非工作时间、家庭选择和家庭安排缺乏直接控制权,也反对把家庭看做是服务于资本家的功能主义观点。除了偏远地区的公司市镇以外,雇主似乎并没有想争取这种控制权。这种家庭形式也和资产阶级家庭价值观在工人阶级生活中不可避免地扩大无关。包括继承权在内的资产阶级家庭的关键要素,对绝大多数无产者来说都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意义。这种家庭形式是阶级斗争的偶然结果。
工人运动的一切因素,也包括男性养家糊口的家庭形式,从来都不是普遍共有或普遍可获得的,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它才是大多数无产者有可能获得的。但在1880和90年代,采纳这种形式的渠道在美国和欧洲的白人工薪阶层中迅速增加,并成为许多稳定的工人阶级社区的主流家庭形式。也有许多工人阶级家庭被落在了后面。最底层的工薪阶层家庭,从来就无法单靠一份工资的收入而生存,这就要求母亲们继续从事非正式的有工资工作,或者在工作和抚养孩子之间找平衡,忍受着富裕邻居的评判。工人可以愉快地把自己和流氓无产阶级和殖民地臣民作对比。这基本上是一种种族化的异性恋本位(racial heteronormativity)的逻辑,一种把性偏异者和性工作者排除在阶级的自我观念之外的逻辑。换句话说,随着工人运动的兴起,资本主义下的核心家庭不再如马克思和恩格斯理解的那样,被看做主要是资产阶级的体制,而开始体现并标定出文明的白人和未开化的其他人之间的区别。到了19世纪中期,性工作者和酷儿与同阶级的其他群体之间的社会融合发生了转移,性偏异者越来越成为被排除在体面的工人阶级生活之外的弃儿。
第二国际中有关家庭的矛盾
工人运动的家庭取向具有两面性。对男性养家糊口形式的范式性追求,和另一种矛盾的、塑造了为性别而斗争的驱动力构成了张力。工人运动认为,社会主义平等基于无产阶级化的共同经历,这为通过女性就业和再生产劳动的集体化而积极消灭家庭的主张提供了内在依据。男性养家糊口的家庭形式为社会主义运动提供的合法性和稳定性,与普遍就业的平等性之间的张力,塑造了工人运动进程中有关家庭的争论和斗争。
无论第二国际的社会主义者们对妇女就业的立场如何,他们都完全放弃了消灭家庭的号召。欧洲最大的群众社会主义党——德国社会民主党(SPD)最有影响力的理论家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解释说,尽管资本主义正在破坏工人阶级家庭,但人们可以确定社会主义者绝不会在政治上攻击家庭:
一个最常见的反社会主义的偏见在于这一个看法,即社会主义提议消灭家庭。没有哪个社会主义者会有一丁点想消灭家庭,也就是在法律上强行解散家庭的想法。只有最严重的误读才会给社会主义安上这样的意图。[35]
女性对德国社民党的发展和效力至为核心。她们也成为德国社民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起党在社区的基层结构时最积极的志愿组织者。在世纪之交的德国,最畅销的社会主义书籍不是《共产党宣言》,也不是考茨基的《爱尔福特纲领》,而是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 Bebel)的《妇女与社会主义》。倍倍尔在该书中复述了性别压迫的漫长历史,并预言了一个性别平等的社会主义未来。性别压迫是第二国际这个最大的社会主义组织中群众基础的主要关切点,因为性别恰恰是无产者理解资本主义压迫和社会主义解放的主要形式。
女性在社会民主党中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其中包括克拉拉·柴特金(Clara Zetkin)和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爱琳娜·马克思(Eleanor Marx)在第二国际的英国分部也倍受尊敬。尽管在德国社民党应该如何关联女性议题方面存在许多大的分歧,但女性们对女性平等的研究很有热情,并成功说服德国社民党增加了一条立场坚定的女性权利政纲。女性就业问题是核心。第二国际的女性倡导者就一系列问题展开了争论,包括女性的劳动力参与率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女性进工厂工作是否对对阶级事业有害,家庭主妇在组织行动中是否构成重要部分,以及妇女就业对她们的平等是否至关重要。
罗莎·卢森堡把她对女性权力的主张完全放在女性的劳动参与度上。女性是政治主体,恰恰因为她们有在工作。罗莎·卢森堡认为,无产阶级女性的权利在根本上取决于她们的劳动力市场参与度:
如今,数百万无产阶级女性和男性一样,在工厂、车间、农场、家庭工业、办公室、商店创造资本主义利润……因此,每一天、每一点工业进步都为女性平等的政治权利的坚实基础增添了新的基石。[36]
其他社会主义者则认为,依靠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来实现平等的代价太高了,他们主张社会主义者应主主动限制女性的有工资工作。克拉拉·柴特金反对女性就业时写道:“需要树立新的壁垒来反对对无产阶级女性的剥削。她们作为妻子和母亲的权利需要得到恢复和永久的保障。”[37]
家庭主妇型家庭的体面性深度激发了社会主义者对工人社会的想象。男性养家糊口的家庭以及与之相随的邻里关系,体现了德国社民党声称自己适合执政背后的基础——社会体面。许多工人运动的报纸都赞美“社会主义好妻子”养育“社会主义好孩子”[38]。女性的社区组织是把德国社民党的工会基础扩展进工人阶级生活的大范围政治的主要机制。有关女性的社会主义争论和宣传,强调得最多的是家庭主妇面临的问题,包括消费品价格、社区条件、住房、学校教育、与丈夫的权力动态、家庭内部的工资分配、工人组织内部的决策以及妇女选举权。工人阶级核心家庭形式及其与之相伴的稳定的工人阶级社区,成为把工会权力扩展至社会生活的主要机制,构成了工人运动及其身份的深度。
俄国革命中的家庭
在工人运动期间,“消灭家庭”的诉求有了不同的新含义;这不再是共产主义者为消灭资产阶级社会而进行的斗争,而是通过再生产劳动集体化,实现全面无产阶级化的社会主义愿景。俄国革命期间,存在过在工人运动的逻辑之内消灭家庭的真实尝试。
俄罗斯的小工业工人阶级甚至还不曾像德国和英国的一些同行那样,过上体面的家庭主妇型生活,而且布尔什维克起初也没想鼓励这种家庭形式。相反,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层开始坚信,充分动员女性对俄罗斯革命的成功和存亡来说至关重要。布尔什维克实施了一套涵盖广泛的支持女性的政策,远超欧洲的现有政策。布尔什维克颁令简易离婚、法律上性别平等和允许堕胎。在进步性学(sexology)的启发下,布尔什维克还实施了一套类似的支持同性恋的全面立法,包括废除所有反鸡奸法,这是一项史无前例的举措。在一段短暂的时期内,革命后的苏俄在女性平等方面领先于世界。
亚历山德拉·柯伦泰(Alexandra Kollontai)在早期苏联政府的多个职位担任领导,包括社会福利部门和妇女工作。柯伦泰敦促国家体制全盘承担起抚养孩子、养活工人阶级、洗衣服、打扫房间等各种形式的家务和代际再生产的责任。她号召通过再生产劳动的集体化,消灭作为经济单位的家庭:
共产主义经济舍弃了家庭。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社会向单一生产计划和集体社会消费过渡,因此家庭失去了作为经济单位的意义。家庭的外部经济功能消失了,消费不再以单个家庭为基础进行组织。一个社会厨房和食堂网络建立起来了,衣服的制作、缝补、洗涤以及其他方面的家务劳动被纳入国民经济。[39]
再生产劳动的集体化是消灭家庭的实际的物质性机制,十分关键。通过逐步扩张幼儿园、儿童聚居地和托儿所,“工人国家”甚至在儿童抚养方面也将取代家庭。[40]柯伦泰把这种再生产劳动的转变看做是从根本上改变俄罗斯性别和性关系、建立充分性别平等的一种手段:
不再有对女人的家务束缚。不再有家庭内部的不平等。女性不再需要担心失去生活来源,独自抚养孩子。共产主义社会的女性依靠的不再是丈夫,而是自己的工作。[41]
柯伦泰对于这样一场家务生活的社会革命之后性和性别问题会如何变化,有自己的看法,其中包括高度平权的性别关系、增加性少数群体的权利,以及组织亲密和浪漫关系的新颖形式。如果所有的再生产劳动都完全集体化,那家庭就不再有任何经济功能,变成仅仅是个人的选择。
但这种解放是有代价的,这也是工人运动关于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的必要要求:国家权威下雇佣劳动的普遍化。柯伦泰明确表示,家庭必须被消灭,正是因为它枯竭了工人本可以投入劳动的社会资源:“国家不需要家庭,因为家庭经济不再有利可图:家庭分散了工人对更有用的生产性劳动的注意力。”[42]在柯伦泰的设想中,工厂作为再生产的社会统一体取代了家庭,工作和国家的新暴政取代了父权制。
俄罗斯革命中女性(如柯伦泰倡导的那样)住在在集体住房里、共享儿童保育、在食堂吃饭的文档记录甚少。然而,中国农民在大跃进期间的经历表明,其中的矛盾可能不容忽视。在中国,国家主持的项目同样用住房、食品和儿童保育的集体化取代了家庭。毛泽东曾号召通过集体化消灭家庭:“家庭是原始共产主义后期产生的,将来要消灭,有始有终……现在工人不以家庭为生产单位。”[43]这些食堂尽管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农民家庭中的性别关系,却也成了强制规训的工具,因为厨房管理员在面临稀缺时,越来越根据政治偏袒来配给食物。国家政策加剧了饥荒,农民也不再有独立的谋生手段。1958年至1962年间有超过三千万人挨饿,集体化厨房似乎是罪魁祸首之一。1961年一名政府官员写道,“群众对食堂真是怕极了,恨透了。群众说:‘交朋友交个管理员,吃馍喝汤不作难’……‘勺把子上有刀子’。”[44]
作为在内战期间力求生存的手段,列宁支持柯伦泰消灭家庭的努力,但柯伦泰是唯一一个渴望永久转变俄罗斯家庭的人。随着1922年战争结束,布尔什维克政府撤回了对家务劳动集体化努力的支持,只保留了像托儿所等能让女性在工厂和田间工作的设施。到了1933年,斯大林重新将同性恋定为犯罪,也收回离婚的合法权利,引入了鼓励形成核心家庭的亲生育政策。1940年代柯伦泰在瑞典以大使身份度过晚年,平静地接受了苏联性别不平等被重新强加和核心家庭被巩固。
在布尔什维克的政策中,我们又一次看到了工人运动中有关家庭的核心矛盾:一方面是通过无产阶级化实现社会主义平等和进步的要求,另一方面是依靠核心家庭提供合法性和稳定性的要求。德国社民党倾向于后者,而俄罗斯革命从前一极摆向了后一极。
吉姆·克劳法(Jim Crow)
在工人运动期间,美国巩固工人阶级家庭范式的时候,走的是一条平行但截然不同的轨迹,这条轨迹与吉姆·克劳法、白人财产所有权和郊区化(suburbanization)交织在一起。19世纪末的大多数美国人,无论白人还是黑人,都从事农业。美国东北部正迅速工业化,制造业蓬勃发展,白人劳动力主要凭借他们的欧洲移民身份组织了起来。中西部则是白人家庭经营的小型独立农场的所在地,这些农场是在对美洲土著种族灭绝式的驱赶战争之后建立起来的。19世纪中叶从墨西哥夺取来的西南部地区,在铁路建成后开始与美国其他地区融合,因而涌入了许多从事采矿、农业和畜牧业的白人定居者。南方白人土地所有者击垮了黑人的重建运动,并在1890年代前重新确立了一个新的白人至上主义政权,实行隔离法律、剥夺公民权和持续的种族恐怖,把非裔美国人困进佃农制农业中,并阻止他们从工人运动中获益。美国工人运动是由这种白人至上的逻辑塑造的。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跨阶级的白人种族身份阻碍了大规模劳工运动的整合。西进运动中的定居者掠夺土地,这为白人工人提供了阶级流动的机会,也提供了逃离雇佣劳动、获得独立的可能性。即便对无产者来说,白人身份也是通过拥有财产的可能性,以及对国家主要的土地所有者的认同而形成的。
美国工人运动的这些种族化动态关系塑造了工人阶级的家庭形式。对于白人工人来说,工人运动使之得以可能的父权制家庭,是由社会地位、财产所有权和体面性构成的。黑人工人虽然被排除在这些工人运动的核心特征之外,但他们在此期间也遭遇了家庭范式极剧窄化。然而对黑人家庭来说,父权制范式不是通过体面性,而是通过佃农制的限制强加的。黑人佃农要被迫结婚。白人土地所有者只会把土地租赁给已婚夫妇。棉花农业的范围正在扩大,每块土地都很小,新的黑人家庭只要结婚就可以获得土地,但单身黑人成年人或那些不按常规组建家庭的人却无法获得土地。一旦黑人能逃离佃农制时,他们的结婚率就急剧下降。[45]随着黑人进入工业化城市,他们似乎抓住了逃离异性恋、以婚姻为基础的家庭范式的机会。吉姆·克劳法所强加的不仅是贫穷、种族主义恐怖、政治排斥与法定的屈从,还有十分死板的父权制家庭。因此,后吉姆·克劳法时代黑人结婚率低下(后文将会讨论),其根源或许不仅是贫穷、缺乏稳定工作和被排斥出工人运动的收益,也是对佃农制度下的家庭制度的抵抗与逃离。
与此同时,白人工人阶级家庭从一边倒依赖自家农场,慢慢转向了有工资工业劳动。家庭经营的农场依赖于长期的二元配偶关系。整个19世纪,美国白人占据的土地边界和新的定居地的不断扩张,都允许并鼓励着稳定家庭的形成。其中许多农民家庭都被吸引到社会主义党和其他左翼平民主义政党中,但他们的阶级意识依然无法与致力捍卫财产所有权、定居者殖民主义和白人自主等做法划清界限。19世纪末的以熟练行当为主的白人工会,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资本家和独立农场主的性别保守主义。和他们的欧洲同行一样,这些白人技术工人也粗暴地追求——并且大多在19世纪末获得了——能确保家庭主妇型家庭结构的家庭工资。
和欧洲一样,这种发展中的家庭形式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陷入了危机。两次世界大战首次为许多非裔美国人和女性提供了非农业的就业机会。军事和战争工业施行性别隔离,对同性恋较为温和,首次形成了大规模的美国地下同性恋社区。[46]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人经历了一种与早期苏联社会相当的性别秩序:透过无产阶级化被组织起来、家庭解体、同性恋和女权的空间增加,以及大规模的国家控制。新近无产阶级化的人们还没有融入稳固的、异性恋本位的工人阶级身份,他们在战争年代工业雇佣劳动加国家控制的新暴政之下,建立了前所未有的性自由。
美国工人运动的这种种族化分层一直持续到20世纪。1930年代产业工人运动终于获得力量,却无法在白人至上主义暴力尤为突出的政权下在东南、西南部各州站稳脚跟,如今这些州成了工会斗争不受法律保护的“工作权”州。自第一次世界大战起,随着非裔美国人离开农场,进入雇佣劳动领域,他们发现美国工人运动在各地被接受的程度并不均衡。反种族主义的工会试图实现战后美国的另类设想,在主要的工会化工厂周围建造种族融合的郊区住宅。但是美国白人工人在跨种族团结方面的利益并不统一;许多人捍卫自己利益的时候,利用本土主义、仇外心理和种族主义和利用阶级团结的概率是相当的。
3.对工人运动的反对以及工人运动之后
到1960年代末,全球无产者开始大规模反叛。内战、街头骚乱、大规模学生和工人罢工席卷了每一个大陆。这些叛乱是多重的,反对帝国主义、殖民种族隔离、国家压迫、性别宰治(domination)和资本主义的斗争交错展开。在美国,黑人解放运动成功地推翻了构成吉姆·克劳法、由法定的屈从和暴虐的恐惧环环相扣的种族系统。通过暴乱、黑人权力的组织、勇武(militant)抗议和制度化的政治阶级宣传,他们进一步反抗集中化的城市贫困状况、自己被排斥出工人运动的好处,以及国家的警察暴力与监禁的状况。到了1970年,一种新的反叛形式出现了,它借鉴了黑人解放运动的策略和分析,如今正对工人运动的性别和性制度发起挑战。这些女权主义者和酷儿激进人士试图消灭男性养家糊口的异性恋核心家庭形式,以便实现充分的性自由和性别自由。
这个时代出现了对工人运动中的性别和性规范的三重交错反叛:激进女权主义、同性恋解放和黑人女性组织行动。这些反叛反对男性养家糊口的家庭形式及其暗含的性别和性制度,通过质疑三项原则而拒斥工人运动的性政治:左派信奉的男性气概、异性恋核心家庭和郊区生活的痛苦,以及工作本身。
反对家庭
1960年代末,男女同性恋以勇武的姿态爆发式进入人们的视野,发起了反帝国主义、社会主义、性别越轨和爱欲的激进政治组织。1970年代,同性恋解放团体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主要城市迅速发展。他们共同致力于爱欲愉悦的解放力量。意大利的马里奥·梅里(Mario Mieli)、法国的盖伊·霍奎恩(Guy Hocquenghem)和英国的大卫·费恩巴赫(David Fernbach)等同性恋革命派都把爱欲视为人类自由的潜在的解放源泉,这反映了同性恋解放主义者圈子中的一种普遍情绪。爱欲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压抑和屈从了,被异性恋和郊区核心家庭严格限制,并在肛交的越轨潜能中被释放出来。比起各种共同的本质性身份,爱欲的团结更能为同性恋共产主义提供实践(praxis)。
跨性别和非常规性别的有色人种——其中大多是流氓无产者的性工作者,在1966年旧金山康普顿自助餐厅的暴乱以及1969年纽约石墙暴动(Stonewall riots)中发挥了引领性的斗争作用,随后又通过街头异装行动革命(Street Transvestite Action Revolution,STAR)等团体,在同性恋解放阵线(Gay Liberation Front)中突现出来。在政治动乱和社会动荡的时期,拉丁裔和黑人跨性别女性发挥了尤为戏剧化和有影响力的作用,为新兴的酷儿政治构建了反叛和有起义色彩的一极。玛莎·约翰逊(Marsha P. Johnson)、西维亚·雷·里维拉(Sylvia Ray Rivera)和马杰小姐·格里芬-格拉西(Miss Major Griffen-Gracy)等跨性别性工作者,都成了石墙叛乱中的传奇人物,她们也是1970年代同性恋驯服政策的激烈反对者。里维拉后来反思了石墙叛乱中跨性别人士的边缘性和勇武:
包括我和其他许多跨性别人士都投身于各种斗争。但是在这些斗争中,在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女权运动中,我们仍然是外围者。这些运动之中有一些容忍跨性别群体的唯一原因在于,我们跟工合(Gung ho)一样[47]是第一线分子。我们他妈的不在意别人怎么想。我们没什么可失去的。[48]
1950年代末起,在美国大城市的酷儿群体中最显眼的是有色人种的跨性别女性,这使她们最容易遭遇街头骚扰和暴力。他们一向是警察、主流同性恋者和同为性别激进者眼中偏异酷儿的代表。有色人种的跨性别女性几乎完全被排除在正式的雇佣劳动之外,而要通过街头性工作和犯罪维持生存。她们在美国的许多大城市可能只占数百人,但在更广泛的地下世界中却是核心人物,这个地下世界中有成千个各色各样的流氓无产阶级酷儿,包括其他非融入的(non-passing,【译注】指并不被旁人视作变性后的性别的跨性别人士)性偏异者、无家可归的酷儿人群、有毒瘾的酷儿、性工作者和同性恋罪犯。
这些性别和性激进人士尝试了一系列新的方法获得性快感和家庭安排,包括独身、自由恋爱、排他性的同性恋、集体生活、开放式关系、禁止单偶制、性快感平等化,还有其他许多。同样,1960年代末的青年反叛者哪怕不是女权主义者或者酷儿,也提出了一种对(在工人运动逻辑以及在它的帮助下建立起的社会之外的)非规范性性快感的激进承诺。一些男性主导的极左组织项目、早期女同性恋女权主义者集体、男同性恋解放主义团体以及相关的酷儿亚文化圈子,都以这种性和性别实验为特征。大学生反对男性在女生宿舍过夜的禁令,引发了法国1968年5月的叛乱。自由恋爱、非婚的随意性行为和节育是1960年代反文化嬉皮青年运动的核心,体现了对异化社会的彻底拒斥。以骨干(cadre)为基础的勇武反帝国主义团体,如气象员(Weathermen)和后来的乔治·杰克逊旅(George Jackson Brigade)[49],都强烈反对单偶制范式,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50]从那个时代激进的回忆录和短命的公社中,可以看出人们对于性作为快乐、自由和联系的源泉的生机勃勃的发现。
这些性别和性激进人士一致认为,异性恋核心家庭是一个恐怖和暴政的场所。在绝对反对家庭主妇的境况之为女性受宰制的症结这一点上,女权主义者和妇女解放运动实际上联合了起来。女权主义各潮流的主要区分点,在于其对家庭形式的特殊批判和提出的解决方案。最主流的自由派女权主义者追求劳动力平等,以便让女性能摆脱不良的关系,他们倡导家庭内部的平等,这与几个时代前的工人运动和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者的诉求相并行。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则认为家庭是性别社会化、父权暴政和性别化暴力的主要工具,她们把全盘摧毁家庭作为接近真正自由和解放的必要步骤。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就家庭主妇的角色与资本主义积累逻辑的关系问题展开详尽的论述,在究竟是发起主妇的自治组织行动还是着眼于组织雇佣劳动中的女性之上有分歧(这也是工人运动中的类似矛盾)。所有人都认为做家庭主妇是一种可怕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家庭主妇具体体现了在压迫性的社会中做一名女性意味着什么。
激进女权主义提供了迄今为止关于家庭的暴政的最深刻、最彻底的讨论,指出了家庭的直接宰制、暴力征服和根本异化的性质。是他们首先认识到性暴力在性别关系中的核心位置。他们认为,家庭的隐私性使它免受考察和反抗,这助长并维持了核心家庭中的特殊的恐怖:童年虐待、亲密伴侣暴力、婚内强奸、原子化隔离、反酷儿的恐怖以及强制的性别社会化。艾莉森·爱德华兹(Alison Edwards)认为,女性易遭强奸的直接原因是男性养家糊口的关系对于家庭主妇的无工资劳动的依赖:
许多妻子都是她丈夫的老板的无工资雇员。劳累的家务活反过来又塑造了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小鸟依人的性,柔和的性,愚蠢又无趣的性,唾手可得的性别。正是这些因素形塑了强奸的政治。[51]
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的这些性别及性运动既继承了共产主义遗产,又挑战了工人运动的性别保守主义,从而重新提出了消灭家庭的号召。就这一诉求来说,这两个运动都认识到家庭在性别制度和性别暴力制度中的核心地位,也对历史上的工人运动与资产阶级家庭理想的共谋提出了质疑。许多人认为,压迫是通过核心家庭所强加的规范性性别角色建立起来的。第三次世界同性恋革命运动(Third World Gay Revolution)在1970年的纽约政纲中写道:
我们希望消灭资产阶级核心家庭制度。我们认为,资产阶级核心家庭通过塑造性角色、性定义和性剥削,使同性恋与异性恋的虚假范畴经久不衰。作为资本主义基本单位的资产阶级核心家庭创造出压迫性的角色。一切压迫都源于核心家庭结构。[52]
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和同性恋解放主义者的批判,与他们排斥美国郊区的原子化、孤立化及社会状况是分不开的。他们所批判的家庭的阶级特征是模糊的,因为正是工人运动成功地创造出了一个稳定、体面的工人阶级,而郊区的建设模糊了白人工人阶级、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家庭形式的区别。1963年一部受众广泛的女权主义经典之作《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把孤立的家庭主妇作为分析的核心。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该书从对郊区生活的描述开始:
一个问题多年来一直埋藏在美国女性的心底,无人开腔。二十世纪中叶美国女性忍受着一种奇怪的躁动,一种不满、向往的感觉。每个郊区的妻子都独自在这种感觉中挣扎。[53]
那个时代的激进女权主义者和酷儿在抵抗的实践与分析中提出消灭家庭,至今仍有回响:它体现为试验另类的生活安排和浪漫形式、抗拒一切郊区同化的渴望、拒绝屈从于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要求、拒绝约束性的性和性别角色,以及认为人际关系具有彻头彻尾的政治性。第三世界女性联盟(Third World Women’s Alliance)号召建立一种基于性别平等的广大的公有制家庭结构:
在资本主义文化中,家庭制度被用作一种经济和心理工具,并非用来满足人们的需要,而我们声明,我们不会和任何人对任何人的私有制扯上关系。我们鼓励并支持公有制家庭的持续发展以及大家庭的理念,鼓励父权制家庭以外的另类形式,呼吁男女共同分担(包括家务和照料儿童在内的)一切工作。[54]
这种集体生活安排有时体现为公寓变成无家可归的跨性别有色人种性工作者的非正式互助庇护所,有时是精心安排的、有骨干的高度自律的集体住房,有着对女同性恋-女权主义者的严格着装规范,有时是农村的嬉皮社区。
黑人女权主义者试图解决作为白人规范性机构的工人阶级家庭的历史问题。自1930年代起,随着大量移民来到北方城市,非裔美国人一方面进入了蓝领工薪劳动力市场,一方面又被排除在日益增长的郊区白领就业部门之外。许多人发现自己生活在城市“贫民窟”——集中了贫困、暴力的种族政策、不合标准的住房和不平等的工资就业机会的社区。20世纪60年代中和后期,随着民权运动成功拆除了美国南部的吉姆·克劳法的法律体系,150余个美国城市的非裔美国青年发起了骚乱。这些起义促成了黑人组织重要的重新定位,并引起了联邦政府的密切关注。
政府一个回应是1965年美国参议员兼社会学家帕特里克·莫伊尼汉(Patrick Moynihan)的一份报告,报告认为黑人城市生活的社会混乱是由女性主导的家庭直接导致的。这份报告题为《黑人家庭:国家行动方案》(The Negro Family: The Case for National Action),被称为《莫伊尼汉报告》(Moynihan Report),它做出的评估在种种伪装下指导了许多自由主义社会学家、政策制定者乃至于性别保守的黑人民族主义者的思考:黑人失业率高、犯罪率高和其他社会功能失调是黑人社区中女性主导的家庭过多的结果,这就是所谓的“黑人母权制”;黑人妇女的婚姻和生活方式选择,包括高比例的有工资工作和相对较低的结婚率,都使美国黑人在更广泛的、期待家庭由男性主导的社会中被边缘化,并造成了黑人的男性气概危机及犯罪的不当行为、破坏性的社会抗议和失业的危机。[55]在这里,美国黑人被排除在工人运动特色的家庭形式之外的罪魁祸首被安在黑人妇女头上,与此相反的异性恋本位父权家庭形式则被当做社会秩序的基本条件。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19世纪中期恩格斯以及资产阶级评论家对工人阶级生活的道德失调的恐慌的回响,工人阶级家庭为了适应物质方面的约束,采取了新的形式。
尽管大多数黑人都无法选择男性养家糊口的家庭,但黑人避免结婚的做法也可以被看做是对性自由的积极主张,对父权家庭规范的拒绝,以及对其他形式的家庭结构的提倡。上文提到,逃离了吉姆·克劳法的强制婚姻的非裔美国人中,选择不结婚的比例确实更高。在种族主义劳动力市场排斥下,黑人男性的周期性就业不足也是阻碍婚姻的另一个结构性因素。在吉姆·克劳法时期,被排斥在雇佣劳动之外的黑人无产者也被排除在工人运动之外;随着大迁徙(Great Migration)和吉姆·克劳法的消灭,黑人无产者开始从事雇佣劳动,但他们通常都没有办法(无论他们愿不愿意)建立男性养家糊口的家庭。黑人女性不愿意牺牲独立来换取对一种不可能体面的无望的、半途追赶的效仿,她们通常选择和朋友或女性亲戚一起抚养孩子,而不是和丈夫。弗朗西斯·比尔(Francis Beale)在“双重威胁:做黑人与做女性(Double Jeopardy: To Be Black and Female)”中写道:
想让黑人女性径自按照中产阶级白人的模范照顾自己的家庭和孩子,是一种白日梦。大多数黑人女性不得不靠工作维持家庭的居住、吃饭和穿衣。黑人女性在黑人劳动力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对于最贫困的黑人家庭以及所谓的“中产阶级”家庭来说都是如此。[56]
《莫伊尼汉报告》促成了一些为塑造黑人的性为目的的福利项目。1960年代中期的骚乱极大地增强了政府对“反贫困战争”的支持,包括扩大美国福利制度,把贫困的非裔美国人包括在内。美国的大部分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都是从1930年代开始实施的,当时美国南部的大部分白人所有者仍然依赖着屈从于他们的黑人家庭的劳动力。各种福利制都有意把家庭佣工和农业工人——大部分非裔劳动力所在——并在白人至上主义盛行的地区设置许多政府层面的控制权。1940和50年代,黑人大多被排除在政府福利支持之外。为了平息和控制1960年代的动乱,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开始向失业的单身非裔女性开放机会。
这些妇女在福利部门居高临下的社会控制形式中遭遇了许多挫折。她们很快组织起一个项目网络,也就是之后的国家福利权利组织(National Welfare Rights Organization, NWRO)。该组织由接受现金拨款福利的非裔母亲组成,在1960年代末发起了许多场运动,显著改善了领取福利者的机会和待遇,组织的终极目标是争取数额可观的联邦全民基本收入。她们组织的其中一项很有名的运动直接挑战了对黑人的性的胁迫(coerce)。福利部门不给有“男人在家”的女性提供福利,幻想母亲可以依靠这个男人。为了落实这项政策,福利部门和警察部门合作展开“午夜突袭”,在深夜进行检查,评估福利领取者是否与男性同居或者有性活动,从而没有资格获得福利。NWRO通过组织行动和诉讼成功推翻了这些做法,捍卫了黑人无产者的非婚性关系权利。
反对工作
19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性别激进人士的第三个要点,对该研究至关重要:他们开始拒绝工作。许多女权主义者仍然停留在通过雇佣劳动和国家干预设想平等的框架内,但我们将关注工人阶级女性中的两例更自觉的反工作政治:美国福利权利运动(American welfare rights movement)与家务工资运动(Wages for Housework)。
国家福利权利组织(NWRO)是贫穷的非裔美国人对工作的反叛。[57]黑人工会运动呼吁充分就业和工作机会,而这些工作需求对NWRO勇武派来说几乎没有吸引力。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毕生辛勤工作,却发现自己的工作是没有成就感和异化的。NWRO的资料提供了一个历史论点,认为非裔美国人用好几代受奴役的屈从的劳动建立了这个国家,他们已经工作够了。NWRO组织起来反对低工资和无工资的“工作福利”方案的剥削与残酷。有些NWRO成员强调她们作为母亲的角色就是对社会作出生产性贡献的一种形式,但其他人抵制这种说法,而是主张把“生活权”与工资、工作和对劳动力市场的参与相分离。这些勇武派安排在福利办公室和政府大楼的静坐示威和占领行动,在法庭上动员起来,鼓励福利接受者争取尽可能多的福利,需求把福利系统推向危机,迫使整个系统全盘重组,终结美国现金拨款福利繁琐的经济状况调查、行为规训和督促工作的做法。NWRO的一项核心运动是争取由联邦担保的年收入,或称负所得税(negative income tax),在许多倡议人看来,这是一种结束长期被迫从事不满意的工作的手段。福利权利活动人士号召通过切断工作与生计的联系而结束强迫工作。
这种主张与社会民主主义者长期以来对福利的理解相比有了根本的转变。欧美战后的福利项目主要是作为充分就业的补充而设计的。老年护理、儿童护理、失业保险、残疾保险或公共医疗,都是对终身雇佣劳动的补充。NWRO等等所对峙的扶贫项目的构建用意,是在最大限度上减少与劳动力市场的竞争:福利通常被设置为远低于最低工资的水平,经济状况调查试图排除有就业能力的人,福利领取者会以不同程度被督促过渡到工作岗位。在美国南部,一切福利的渠道都仅限于满足农业劳动力的季节性需求。只有在失业率高和经济危机的情况下,现金拨款的福利额度接近低工资水平才被视为合理的。而对于NWRO和1960年代的其他福利权利勇武派来说,福利不仅是对雇佣劳动的补充,也是逃离雇佣劳动的一种手段。
工人阶级女性运动中的反工作情绪不仅限于非裔美国人的福利权利运动。家务工资运动就无工资家务劳动之苦(作为有工资劳动之苦的对应)提供了最连贯的梳理。1970年代初,意大利工人起义愈演愈烈,家务劳动工资运动也应运而生,并很快蔓延至英国和美国的一部分地区。玛利亚罗莎·达拉·科斯特(Mariarosa Dalla Costa)的《女性与社区的颠覆》(Women and the Subversion of Community)认为,妇女受到的压迫是整个资本主义总体性的总体再生产所产生的,这为后来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奠定了概念基础。该书作出了一个重大的理论突破,就是承认资本主义的再生产同时依赖于有工资的工作场所劳动与无工资的家庭再生产劳动,该种再生产既因为工人运动引发的起义强度而成为可能,也面临自身局限。达拉·科斯特写道,家庭结构“是资本主义工作组织的支柱”[58],它构成了有工资活动和无工资活动之间的鸿沟:“它使男性成为工资奴隶,并且到了成功把这些服务分配给家庭中的女性的程度,而这一个过程还对女性流入劳动力市场加以控制。”[59]
随着家庭主妇型工人阶级家庭的降临,女性被安置进家中,从而生产出工人阶级内部的性别分工。女性的斗争必然要拒绝家庭,与再生产护理行业从业者联盟,发起一场革命性的叛乱:
我们必须走出房子,必须拒绝家庭,因为我们要和其他女性联合起来,与一切认定女性应当留在家里的状况作斗争,与那些贫民窟的人的斗争联结起来——无论这贫民窟是托儿所、学校、医院、养老院还是收容所。消灭家庭本身已经是一种斗争的形式了。[60]
这种反对家庭的斗争在根本上针对的不是雇佣劳动,而是要拒绝工作本身:
女人必须完整地发现自己的可能性——既不是补袜子,也不是当远洋船长。更准确地说,我们可能想希望做这些事,但现在这些活动不能存在于任何地方,而只能在资本的历史中。[61]
西尔维娅·费代里奇(Silvia Federici)的说法也呼应了家务劳动工资的反工作维度:
从这个分析出发,我们可以看到家务劳动工资诉求的革命性意味。通过这种诉求,我们的本性终结了,斗争开始了,因为要求家务劳动工资就意味着拒绝这种被当成表达我们本性的工作,因此也恰恰拒绝了资本给我们发明的女性角色。[62]
无论这对许多读者来说多么反直觉,费代里奇都清楚表明,对工资的诉求也是对拒绝工作的能力的诉求。对于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来说,拒绝工作不是个人刻意逃避工作,而是大规模罢工行动和有组织的阶级叛乱的可能性。在这里,他们的政策建议是一种揭露无工资家务劳动暗含的动态关系的手段。在费代里奇看来,对工作的拒绝是通过工资实现的:“从现在起,我们对每分钟的工作都要求报酬,这样我们就可以拒绝一部分工作,最终拒绝全部工作。”[63]
在这种反工作的视角下,可以把家务劳动工资运动看做是非纲领性的(non-programmatic)。无工资再生产活动后要获得字面意义的经济补偿这种诉求,和这些活动具有生产价值的特点这一宣称,二者都可以看作是他们的挑衅;他们真正的洞察在于其他方面。达拉·科斯特对“家务劳动工资”只是简单提及,并不十分批判。西尔维娅·费代里奇对家务劳动工资的呼吁出自一篇名为“工资对抗家务劳动”的文章。我们肯定,包括塞尔玛·詹姆斯(Selma James)在内许多家务劳动工资运动的提倡者,设想的可能是某种比较表面的东西。[64]
局限与矛盾
19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黑人女性左派、激进女权主义者和同性恋解放者对性别自由的愿景比以前的梳理更深入了。与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前辈不同,他们承认工人阶级家庭是个人屈服、暴力、野蛮和异化的场所。在他们的理解中,阶级本身的自我活动通过直接建立替代性的亲属关系和互助关系而成为消灭家庭的主要机制。尽管时有反复,但他们也开始认识到帝国、郊区白人、制度化的工人运动和异性恋本位的父权制家庭的关系。他们渴望一个相互照顾、相爱、爱欲的愉悦、共同斗争和个人转化,而不是孤立与控制的广阔的公有场所作为家庭。
在推进对胁迫性二元性别表达和规范性性别期望的批判时,他们开始把性别和性身份的消灭憧憬为消灭家庭的终点。他们认为消灭家庭的斗争需要个人直接改变他们对其他人的期待和行为,推进并加深之前关于男性沙文主义妨碍阶级斗争的社会主义批判。1970年代的性别激进人士在处理经济生存和工作时,开始朝拒绝工作迈进,朝渴望摆脱雇佣劳动的束缚迈进,而不只是想象通过普遍的无产阶级化实现平等。
然而他们的政治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是不够的。激进女权主义者和同性恋解放主义者打造的解放愿景,已经不再能像它们在1970年代初采取的形式那样,激起大规模的性别叛乱了,在之后几十年间的性别思想和斗争中,也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即使是有效提出了在今天依然能引起回响的家务劳动工资运动,所回应的那个世界也早已不同。
激进女权主义者和同性恋解放主义者的分析,是从对原子化的异性恋核心家庭批判出发,推断出对整个社会的整体理解。他们认为父权制是军国主义的根本基础,同时巩固了独裁国家、法西斯主义、殖民主义、性暴力、性别规范和私有财产。激进女权主义者把女性遭受的压迫安放到性-种姓或者性-阶级体系中。此时女性构成了一个连贯的社会群体,具有一套易于整合的统一利益——就像早期工人运动所想象的工业无产阶级那样——并在家庭中遭受独特的压迫形式。这种性-阶级分析一贯地反思了他们自己被压迫的经验,主要是白人妇女对于受困于郊区家庭的抵制,但严重误读了家庭在资本主义中的位置。
尽管在封建制下,国家组织、经济和父权家庭之间曾经有同义且直接的交错,但在资本主义下,这些系统都被雇佣劳动局部分割开了。也就是说,不再需要靠直接宰制和暴力来从生产过程中榨取剩余价值,政府事务和家庭的动态关系从而具备相对的自主性。资本主义制造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实际上分离,将某种性别宰制形式隔离在家庭的私人墙壁内。而政府或企业中普遍存在的男性宰制形式,无论表面上与家庭的性别动态有多么相似,也具备一种根本上不同的特征,并将一贯的“父权制”打散了。从批判家庭开始推论的做法,最终使激进女权主义者无法充分把握资本主义和种族国家的动态关系。
通过性-阶级分析来理解女性的压迫,会导致激进女权主义者陷入许多死胡同。事实表明,他们无法有效解释或回应迸发的关于女性之中阶级和种族差异的辩论,因为他们的策略和愿景都离不开省略女性之间实质的阶层化。跨性别女性与激进女权主义一道政治化,她们最初在女权主义阵营中很活跃,却很快遭遇了强烈敌意,因为人们揭示了性-阶级分析要依赖基于生物学或早期社会化的二元对立。激进女权主义者早期对性愉悦产生过敌意,认为它与父权压迫有内在的纠缠不清,这引起了1980和90年代迸发的所谓“性战争”的争论,并在关于色情、性工作和性癖(kink)的争论中持续。
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和黑人女权主义者对性-阶级模型提出了初步的质疑,指出它无法解释女性之间的差异,以及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现实。然而除了极少数情况以外,他们也无法为家庭内部的屈从经验提供一种有意义的替代性解释。黑人女权主义作品通常把家庭定位为反抗的中心,而低估了性别胁迫的作用,正是性别胁迫的存在使得1960年代起许多黑人女性避开异性恋配偶家庭的结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要么依赖理论上薄弱并矛盾的对于劳动女性被压迫的二元制(dual-systems)论述,要么陷入无工资家庭主妇的工作是否产生价值这场持久又累人的争论。在一些短期的自治项目之后,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最终重新回到了社民政治或者列宁主义政治。1970年代初的黑人女性作品同样深受民族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政治的影响,这些运动陷入了其他有迹可循的矛盾之中。
同样,同性恋解放主义者也无法提出一个在能在今天引起足够回响的纲领。在艾滋病肆虐之前的整个1970年代,一些大城市的男同性恋者几乎已经能自由地频繁获得色欲愉悦了。尽管人们可能会怀念这一时期的愉悦和自由,但如今很少有人会设想它们提供了一条通向自由社会的道路。1970年代,酷儿和异性恋者的性规范一起急剧松绑,这表明性压抑实际上并不像早期的爱欲力量的捍卫者主张的那样,是资本主义宰制的凝聚力。新左翼重塑异性恋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可以说是可怕的,勇武派奋力“粉碎单偶制”,却让自己落入越来越详尽的各式厌女和创伤。如今,性在流行消费文化当中四处横行,它既是是一道新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对享乐的艰难禁制令,也是自由的源泉。当同性性行为被严重定罪时,追求情色可以凝聚起新的革命团结这种想法可能还有意义,但现在它已经不再是鼓舞性的政治,可以引发回响了。
激进的酷儿和女权主义者试图摧毁和攻击规范性的核心家庭形式,但他们从未能够梳理出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连贯愿景。许多人在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组织的项目中进进出出,或者把他们的性别反叛当做他们反资本主义分析的直接拓展。那些最沉浸在马克思主义政治中的同性恋和女权活动人士,在把握或参与最动态、最越轨和叛逆的酷儿及妇女斗争时显得相对无能。比如,同性恋的托洛斯基主义者和资产阶级同性恋者一道设计了基于权利的同性恋运动,以此拒绝作为亚文化的“性别互混(genderfuck)”同性恋解放政治,认为它属于极左。相比之下,1970年代早期女权主义和酷儿运动中的社会主义和反资本主义愿景往往相当模糊,所借鉴的是反殖民的第三世界马克思主义中的浪漫主义观念。
1970年代早期以来的运动中,这种有关性和性别解放的观点的不充分性也影响到他们消灭家庭的设想愿景的局限。他们憧憬的消灭家庭,是通过有意的亚文化刻意追求的一种活动。他们几乎看不到把家庭的消灭普遍化,达到全社会范围内的经济关系重构的可能性。这一局限最终体现为工人运动的视角始终存在。即便他们试图避免工人运动的男性化,避免它对工资劳动的狭隘关注或者局限于无产阶级化的平等视角,他们也无法憧憬消灭阶级关系本身。工人运动透过将雇佣劳动条件普遍化而寻求社会主义自由,而在雇佣劳动的条件下,家庭只能通过另一种非市场制度——国家——的大幅扩张来解体。这些年轻人试图逃离雇佣劳动,却无法憧憬除了这样那样的工厂以外,还有什么集体的共产主义社会再生产的手段。“共产主义理论”小组(Théorie Communiste,TC)指出了这种反对并批判工作的政治,与对工人运动的超越之间的区别: “‘对工作的批判’无法将重构积极地看作阶级间矛盾关系的改造”,这使得五月风暴中的叛乱者陷入他们本想拒绝的肯定性工人身份逻辑之中。TC的艰涩语言也适用于1970年代初的性别反叛的局限:
对工人阶级境况,以及对生活各个方面的反叛陷入了分歧。它只能先背离自身的基础(也就是工人的境况),才能表达自己、发挥效力;但这样做不是为了抑制这些境况——因为它没能在自身中发现那种本可以成为该种抑制的与资本的关系——而是为了把自己同这些境况相分离。因此“五月风暴”只停留在反叛的程度上。[65]
新左翼中确实存在的性别与性关系,其中有许多错误被后来的女权主义者、酷儿和反种族主义思想意识到了。1980至90年代参与性别和性政治问题的知识分子思潮大多是学术性的,它们被冠以不同的名字,比如后结构主义、黑人女权主义、有色人种女权主义、性积极女权主义(pro-sex feminism)、后殖民女性主义、酷儿理论和跨性别研究。尽管今天有一些左派大力鞭挞其中的观点,原因包括其中程度不一的唯心主义、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缺少连贯论述、过分强调个体经验、疏离群众运动等等,但是这些知识分子思潮实际上给性-阶级理论、革命民族主义和同性恋解放主义的失败提出了广泛、严格且大多具有价值的批判。1990年代的艾滋运动(AIDS movements)借鉴了福柯和酷儿理论,21世纪以来的跨性别斗争受到了多种理论思潮的启发,美国的“黑命攸关”(Black Lives Matter)运动的勇武派也认同自己受到与之交叉的黑人女权主义的启发。所有这些运动都透过与学术思潮的密切对话,在性别政治方面取得重大政治和理论突破。对于关心共产主义革命的人来说,这些学术工作的局限性显而易见,尤其是它们缺乏对资本主义的连贯批判。但今天我们的根本任务在于整合,而不是全盘拒绝它们思考并超越1970年代运动的性别政治时的努力。
在当下要号召消灭家庭,不能只是重复恩格斯、柯伦泰或者第三世界同性恋革命。无论这些历史案例多么具有教育意义,今天的人们依然需要一种能超越先前反家庭运动的局限的共产主义女权主义。为了做到这一点,如今关于家庭的共产主义理论工作必须解释1970年代以来工人阶级代际再生产的结构性转变,尤其是男性养家糊口的核心家庭的衰落,以及性别范畴的碎片化。现在我将转向这种转向中的政治经济学。
在男性养家糊口的家庭之后
上述运动的积极革命愿景最终溃败了。到1970年代末,席卷全球的起义已经被压倒性粉碎。这些政治失败尽管有各自不同的政治背景,却都根植于一场更广泛的资本主义利润力危机中。[66]1970年代的性别反叛者也经受了运动的急剧衰落。女权主义者在目睹了1970年代女性平等由于经济变革和立法胜利而取得重大进展之后,又面临着政治的反弹和性别工资差距的延续。同性恋解放运动的能量放缓了,在1970年代缩减成一种狭隘的基于权利的倡议运动,只有在1980年代末的艾滋病危机高峰期间才重新进入勇武阶段。到了1970年代末,福利权利倡导者也不再有进展了,很快就经历了新的紧缩时代下现金拨款福利和社会服务的大规模解体。
随着1970年代中期更大的一波斗争崩溃,这些运动的羸弱后人越来越着眼于与一切阶级政治相分离的性别,进行理论化并为之组织行动。与群众的经济诉求切割之后,女性和同性恋权利运动继续在法律平等方面取得一些更为有限的进展。更重要的是,这些性别运动转变了年轻女性和酷儿的期望以及人际动态关系。现在大多数年轻人都欣然接受非婚性行为的权利,也相信家庭可以采取多种可接受的形式。他们有更大机会接纳同性关系以及非常规性别。对个人幸福的关注最有可能引导他们在性和性别方面的决定。
然而随着激进运动的溃败,这些运动反对的家庭形式的关键特征却发生意外的转向。1970年代中期以来旷日持久的利润力危机和工人运动溃败,最终让大部分工人阶级无法承担起一名无工资家庭主妇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后果。让这种家庭形式进入危机的不是酷儿或女权主义者。男性养家糊口的家庭形式在社会的任何部门都已不再典型,并由于同时出现的几种趋势发生聚合而早已丧失社会领导权。我们看到,取而代之的是双工资家庭、选择不找伴侣或不结婚的人、原子化和碎片化的家庭结构,以及成为市场中商品的再生产服务等急剧且稳步增长。这些动态关系共同生产出工人阶级生活中一个异质的家庭形式序列。工人运动诞生时,当时的工人组织在为工人阶级家庭主妇创造优越条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现在情况不同,家庭主妇衰落主要依赖一系列结构性力量。
在反叛的女权运动失败后的几十年间,女性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已婚女性大量进入劳动力市场。自1920年代以来随着白领职位的增加,女性的劳动力市场参与率也逐渐提高。在郊区化高峰期的1950年代,年长女性大量开始工作。随着1960和70年代越来越多的年轻已婚女性也开始工作,这种转变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和确定了。对于在美国有丈夫的已婚女性,她们的劳动力市场参与率从1960年代的30%稳步提升至1990年代的60%以上[67]。尽管劳动力市场法规的持续存在减缓了欧洲社民国家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率的增速,但经合组织国家(OECD)的女性就业率仍在稳步攀升。在英国,女性就业率从1961年的37%上升到1990年的53%,之后一直保持在55%左右。在德国,女性就业率从1970年的39%上升至2016年的56%,这也是实际工资下降的时期。[68]
促使女性越来越多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因素有很多,包括再生产服务劳动、白领职位、教育和医疗保健领域等女性化岗位增加,生育率下降,兼职工作机会增加,以及女性越来越渴望工作。在许多行业和国家,对已婚妇女就业和母亲就业的禁令在1960和70年代被取消了。对工人阶级家庭来说,女性就业最重要的因素的是经济必要性。1970年代以来,工人阶级的工资出现停滞和下降,为了维持相当的生活水平,绝大多数工人阶级家庭就需要把妻子送进劳动力市场,并累积高筑的家庭债台。工人阶级家庭再也负担不起家庭主妇型家庭了。资本主义已经摧毁了作为工人运动的体面性核心的家庭主妇家庭。
随着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经合组织国家的民众开始选择晚婚、不结婚同居、更快离婚以及单身生活。在美国,15岁以上人口的毛离婚率从1950年的3.5‰上升至1985年的6.3‰;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离婚率同期从0.9‰增至4‰。[69]1950年,家中只有一人的欧洲家庭只占10%;到了2000年,这一比例在英国上升至30%,在瑞典上升至40%,欧洲这一比例最低的是希腊,为20%。[70]较高的离婚率可能意味着男女双方都能离开糟糕和不圆满的关系,追求更好的性和非传统的家庭结构。这也加剧了社会生活的原子化、孤立化和碎片化。
夫妻生育的孩子更少了,开始生育的年龄更晚,结束得更早。各地生育率都下降了:从1900年到2000年,德国的儿童与女性比例从5.0降至1.3,美国从3.8降至2.0,印度从5.8降至3.3,拉丁美洲从6左右降至2.7。[71]婚外生育的概率也增加了。从占活产的百分比来看,婚外生育在英国从1960年的8.0%上升至2000年的39.5%,在美国从5.3%上升至31.0%,在前东德从11.6%上升至49.9%,在前西德从6.7%上升至17.7%。[72]较低的生育率意味着人们开始把更多的时间花在生育、住房和狭小的核心家庭界线以外。
除了工资停滞之外,资本主义长期危机的另一个因素也导致了男性养家糊口家庭形式的衰落,并同时影响了其他许多因素:这就是再生产劳动的商品化。随着制造业等许多行业的利润率下降,资本投资逐渐转向消费者服务行业寻找新的机会,这使营利性企业和工资极低的工人(他们提供的服务原本是由无工资主妇完成的)大量增加。甚至许多工人阶级也可以把衣服送去自助洗衣店,把孩子送到日托中心,在快餐店吃顿饭,并付钱让其他工人打扫房间。这增加了女性化行业的就业需求,也为工人阶级女性和酷儿提供了更多的工作机会。富裕的家庭雇佣移民家庭佣工来打扫房间、抚养孩子的比重,是19世纪中期以来从未有过的。通过把再生产劳动外包给有工资服务业,人们可以为高要求的工作周腾出时间,并减少对家中无工资劳动的依赖。
总的来说,这些变化都意味着所有人更有能力走出家庭和社区的狭隘期待,追求更圆满的关系。这些因素可能是追求同性关系、性别重置和复杂的非传统家庭的人数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从许多方面来看,人们寻求关系时导致的上述剧烈的人口分布转向,说明人的性别和性生活质量也有了实际的质的提高。今天的年轻人活在一个比他们的祖父母拥有更多性自由的世界里。
但这些转变也意味着对工资的依赖加剧。男性养家糊口的工人阶级家庭形式的衰落,使女性和酷儿的经验从依赖丈夫或父亲的个人宰制,变为依赖工资的非个人宰制。他们逃离了父权制家庭的暴政,却发现自己成了大城市街上无家可归的酷儿青年,成了注定长期贫穷的单身母亲、在低工资服务行业工作的上百万酷儿和女性的一员,或是处于工资经济边缘的非正式工人。每个人都被迫找工作和维持工作,不断和其他无产者竞争,并受制于雇主和工作过程的性别与性规训。正如工人运动的一系列胜利使男性养家糊口的家庭得以可能那样,旷日持久的经济危机和工人运动的崩溃也使人们陷于物质匮乏、市场依赖和异化工作。新的异质家庭结构既是关照的实践,也是绝望的一种症状,在这种市场依赖中,每个人都遭受新形式的捕猎。一个酷儿青年从与父母的暴力关系中解脱出来,却可能面临街头性工作的新风险;年轻的母亲选择不与虐待她们的男朋友结婚,却可能会发现自己要在性骚扰的经理的手下长时间地在零售服务业工作。
在这些经济趋势下,工人阶级更有可能像19世纪那样,依赖于碎片化的、广泛和异质的亲属关系。各个社会阶级的父母离婚和再婚率都很高,这产生了所谓的继子女混合家庭。有亲戚被监禁的母亲(这在非裔美国人中尤其常见)可能会和姐妹、母亲或者好朋友一起生活和抚养孩子。移民会把一大部分工资寄回给他们原籍国家的家庭成员。他们可能会从长期汇款中受惠,比如希望退休后住在农村的社区,有由家人购买的土地或住房,随后由子女抚养,但这种个人物质好处可能不足以说明迁徙工人汇款回家的金额之高、持续时间之长。同性家庭越来越普遍,包括具备从事雇佣劳动的渠道、对同性恋的惩处减少、公共接受度的提高等因素,都使同性配偶更能融入各自的阶级氛围。同性配偶也更有可能扎根于异质的酷儿依赖网络中,包括前爱人、继子女和异父母的孩子、亲密朋友,以及其他后天选择的亲人。
当然,这些都是家庭的形式。它们都是对日益恶化的经济条件的适应性反应,是满足人们物质和情感需求的繁衍与生存策略,也是个人宰制与暴力的潜在空间。这些模式半选择的特性——它们不是那么被社会期望和自然化的血亲关系的压力所指定,而且和此前时代相比展示了更多抽身的机会——在边际意义上提供了更多抵抗异性恋本位和父权制暴力的手段。在如何更理智、更合适地相互关照而少一些伤害方面,酷儿和酷儿的反文化可以给人们提供许多启发。然而,这些被选择的家庭形式依然活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受到雇佣劳动的残酷性的制约和扭曲。在经济的制约下,关爱友谊的扩展网络常常会崩溃。比如在酷儿的反文化中,人们为了工作而搬家甚至生孩子都经常会破坏互相关怀的长期友谊网络。这样的生活仍然被阶级和种族分层所区隔,相互关怀的愿望甚少能度过严重的吸毒、长期失业、监禁或精神疾病的危机。在这个世界的残酷面前,酷儿、女权主义者和黑人左派渴望彼此的爱与关怀,但这在普遍化的市场依赖的条件下是无法实现的。今天的酷儿群体既没有,也不可能预示共产主义。
对于那些在历史上被排除出工人运动的人来说,减少家庭依赖加剧了工作不稳定(precarity)和国家暴力;在稳定的白人工人阶级那里,这意味着经济不稳定影响下的性别与性关系的大规模重组。这里有一些线索,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极右翼日益增长的男性复仇主义、1970年代后把异性恋家庭作为社会秩序基石的保守宗教运动的增长,以及在原子化的男性在线社群中滋长的对女权主义者的暴怒。家庭主妇和提供家庭工资的工作曾经给男性提供了尊严;提供了一个能让无产者展现性和性别幻想、满足尤其是男性的性与情感需求的受保护的场所;一个逃避雇佣劳动考验的避难所,并确保了另外有人从事再生产劳动。多少代无产阶级的男男女女都为这种家庭形式奋斗,成功并去保卫它,而现在它不复存在。有些人认为酷儿女权主义政治承诺了更伟大的人性,也有些人开始投向愤愤不平的郊区白人男性阶级提供的厌女方案:法西斯组织、非自愿独身者(incel)讨论区、YouTube上的自助厌女频道、社民播客上反女权主义的笑料,或者公开夸赞自己是强奸犯和性骚扰者的政治家。
在本文追溯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个历史中,家庭向来被用作攻击某一部分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武器。在恩格斯那里,这体现为对危机中的工人阶级所谓的性堕落的恐惧;在工人运动那里,它被用来支持体面的男性养家糊口的家庭和谴责它的对手——包括流氓无产阶级、酷儿和黑人工人阶级家庭。资产阶级及其盟友总是谴责贫困的家庭,把种族仇恨与对穷人在受制约环境下的再生产战略、所谓的性放纵和性别不规范的谴责联系起来。
家庭作为社会范式的文化及意识形态功能如今仍然存在,一系列多样的政治斗争把它用于相当反动的目的之上。家庭在当代政治想象中的地位被夸大,正是因为让作为工人运动基础的男性养家糊口家庭形式具有吸引力的那些因素持续存在: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碎片化、原子化和孤立下,家庭具有宣扬道德与社会和文化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力量。家庭被想象为社会秩序和道德的基础,由此带来的重要性有多种表征形式。宣扬家庭的重要性是右翼和新保守主义政治的一个常见特征,也常被各种宗教原教旨主义挪用。父权制核心家庭是右翼宗教运动愿景的社会秩序的意识形态基石,这些运动不断对同性恋和妇女权利的成果发起攻击。宗教保守派和许多社会科学家一样,相信稳定的异性恋夫妇是养育有道德、在社会上正直的孩子的基础。社会科学投入的研究依然汗牛充栋,要竭力表明非传统的养育方式——尤其是在穷人和黑人那里——是犯罪和许多其他社会弊病的原因。主流同性恋活动人士强调说,他们稳定正派的家庭安排也是可称为“同性恋本位(homonormative)” 的政治的核心部分。所有这些表征——宗教保守派、社会科学家和同性恋本位的同性恋——都关注稳定的配偶关系是养育子女的基础,并全力实现性别规范的承诺。这些政治潮流证明家庭可以成为保守的力量。考虑到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原子化、依赖性和家庭财产的动态关系,这些主张并非毫无道理。消灭家庭的号召就是与这种意识形态保守主义对峙。
家庭主妇型的家庭形式已经被资本主义的发展本身破坏了。消灭家庭的诉求已不再直接针对某种特殊的阶级再生产战略特有的某种特殊特定的家庭形式。但是,核心家庭这个暴力和相互依赖的矛盾场所仍然存在。在今天持存的家庭仍然是近乎排他性的代际再生产的制度,也是无产阶级生存所需的雇佣劳动的不稳定之上的附属品。
今天的共产主义者再次发起消灭家庭的号召。[73]如今工人阶级的再生产具有特定的物质条件,这也使该号召与以往的时代截然不同。随着工人阶级的生活日益原子化,消灭家庭的号召在当下也是对社会贫苦的私有化的对峙。工资增长停滞、工作制度强化、社会工资底层架构解体所组成的慢性经济危机,再加上资本主义生活的异化和孤立,迫使无产者寻找生存方式和情感避难所。碎片化的浪漫结合、孤立的养育单位,以及尝试重建与核心家庭似是而非的东西,这些都是最有可能采取的逃避形式。
与1980和90年代的学术酷儿理论家不同,新的消灭家庭的号召总与共产主义的革命规划相关。这些号召各自尝试以各种方式,透过1970年代以来家庭的政治与经济转型来解释性别关系的根本的碎片化。它们的指向是通过非市场的集体性制度承担再生产劳动,从而消灭作为再生产单位的家庭。它们各自寻求重构代际再生产活动的手段。消灭家庭的诉求可以再次为摆脱当今的贫苦提供一条道路。
在此之后:家庭的消灭与共产主义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的再生产依赖于以家庭为中介的雇佣劳动。无产者为了生存,一般必须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给资本家。无法做到这一点的人(包括婴儿)则依靠他们与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其他人的家庭联系。除了家庭的工资渠道以外,儿童还依赖着相当数量的再生产劳动。这些再生产劳动中的绝大部分始终是,而且依然是无工资的。家庭,尤其是异性恋核心家庭,已经成为资本主义下无产者最稳定的主流代际再生产方式。社民国家和认同社会主义的国家有时会扩大并接管家庭再生产中的很大一部分,但这只是补充占主要地位的工资依赖。在有些时候、有些地方,资本主义下还存在着其他的代际再生产及日常再生产系统,如孤儿院、寄养和收养、单亲与大家庭系统,而对于已经度过童年早期的人来说,还有监狱、军队和工人宿舍系统。然而,这些制度离完全取代作为代际再生产的主要单位的家庭还差得很远。今天,有工资的和商品化的再生产劳动虽然扩大,但还没有延伸至大部分初期的儿童养育劳动,还有许多家务劳动和再生产劳动是无工资的。已经商品化的儿童养育活动,也仍然依赖与雇佣工人有纽带的家庭去支付照料的报酬,这改变了家庭依赖关系的花名册。
在这种资本主义条件下,性别和性自由在根本上是受制约的。性和性别成了胁迫与暴力的手段,而不是人类繁荣的源泉。性别和性自由的缺席限制了所有人自由发展与表达福祉,使我们丧失表达完整性别和获得满意的性关系渠道。家庭提供了人们需要的关心与爱,却以个人宰制为代价。在家庭内部,儿童既受到父母的爱和照顾,也受到他们的任性偏见和宰制,被隔离在原子化的住房单位里,而这个单位就是要限制外部以儿童的名义进行干预。资产阶级的子女受继承和财产的承诺约束;而即使无产者能得到的资源有限,许多人在失业或残疾时也要依赖家人支持,或者提供无工资的、但在经济上必需的服务,比如照顾孩子。无产者的孩子足够大的时候就可以离开家人,获得一定程度的独立,但却只得依赖雇佣劳动才能独立。工作本身是一套针对所有无产者生活的复杂的性别与性规训,包括强制的着装规范、劳动过程本身的性别化、服务业中的情感劳动、工作场所的性暴力,以及尤其是雇主的任性偏见。在资本家主宰人们生活的社会中,性别自由是不可能的。在某些情况下,无产者可以依靠国家,实现在家庭或雇佣劳动之外的生存——通过现金拨款福利、国家提供的住房和医保,或者监狱。然而所有这些制度都被用作性别规训系统,把统治阶级及其附属专家的集体偏见强加于穷人的生活。
这种建立在家庭、雇佣劳动或国家依赖之上的无产者性别暴政,在非融入的跨性别者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跨性别者在家里面临父母或其他家庭照顾者暴力的比例更高,并经历着高比例的就业歧视与工作场所中各种形式的骚扰和暴力。工人阶级的跨性别女性经常会因此被排除出雇佣劳动。当失业的跨性别者为了生存而求助于国家,便会面临暴力、被医保拒绝,以及流浪收容所、监狱或戒毒项目强加的性别着装规范,在这些地方,性别规范是制度性合规观念的关键。尽管跨性别女性已经能从一些有限的社会福利项目中受益,但对非规范性别的人来说,国家绝非可靠的盟友。
性和性别自由必然意味着,人们如何选择组织自己的浪漫生活、亲属关系网络和家庭安排不应影响到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物质的富足。因此,性别自由需要生存与再生产资料不依赖家庭、雇佣劳动或国家,而是有广泛的获得渠道。生存资料既包括住房、食物、卫生、教育等再生产的物质方面,也包括人们现在主要从家庭获得的爱与关怀这些情感性的人际纽带。共产主义下的关怀会成为人类自由的一个重要维度:相互关爱和支持的关怀,养育孩子和照顾病人的积极劳动的关怀;爱欲联结与愉悦的关怀;互助以实现透过无数方式所表达的人类巨大潜能的关怀——包括透过如今称为性别的自我表达形式。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关怀是一种商品化的、屈从和异化的行为,但它的内核是一种非异化的相互依赖与爱。积极的自由是通过普遍的物质基础保障基础,和以爱为核心、支持我们共同的自我发展的酷儿和女权主义文化转变促成的。
与当前的反文化组建替代性家庭的尝试不同,消灭家庭是在依赖共产化和抑制经济的同时,对社会再生产的物质条件进行一般化重构。爱与家务的共产主义再生产单位必须为所有人取代家庭,通过斗争的条件探索并建立起新制度。与之前的时代把消灭家庭当作诉求不同,我认为共产主义的性别自由必然要同时消灭雇佣劳动和国家。尽管我在这里没有讨论具体的模式,但我猜测这样的共产主义家务单位可能和傅立叶的一些愿景类似:人们住在几百人的公社里,他们把再生产劳动集中化,共同抚养孩子,也对性预约和性满足有一定关注,力图满足每个人的人际和发展需求,同时不打破个人选择的情感、浪漫或父母纽带。[74]
对家庭的积极超越,就是对共度艰辛的无产者在彼此身上找到的真爱和关怀的维护与解放:爱欲的趣味和欢愉、养育子女和浪漫关系的亲密。这种爱和关怀经过改造和普遍化后,将在家庭宰制被消灭之后保留下来。从异性恋本位的性别与性身份的僵化社会角色中解放出来,从资本主义的物质制约中解放出来,在激烈的革命斗争中经过重塑后,爱和关怀的潜力最终可以释放到世界中。消灭家庭必须等于积极创造一个人类关怀与酷儿爱情普遍化了的社会。
回到本书主页
[1]【译注:原文为 ME O’Brien, “To Abolish the Family: The Working-Class Family and Gender Liberation in Capitalist Development,” Endnotes 5 (2019)。苏子滢译。本文2021年载于澎湃新闻·思想市场,现修订部分翻译。】
[2]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ECW 6,第501页。
[3]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MECW 4,第332页。
[4] 以下史实来自沃利·塞科姆(Wally Seccombe),《历尽艰辛:从工业革命到生育率下降的工人阶级家庭》(Weathering the Storm: Working-Class Families from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o the Fertility Decline),Verso,1993;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扭曲:同性恋常态与酷儿反资本主义》(Warped: Gay Normality and Queer Anticapitalism),Brill,2015;约翰·德埃米利奥(John D’Emilio),“资本主义与同性恋身份(Capitalism and Gay Identity)”;杰夫·埃利(Geoff Eley),《铸造民主:1850-2000年间欧洲左翼的历史》,Oxford,2012;爱丽丝·埃科尔(Alice Echol),《敢于坏:美国激进女权主义,1967-1975》,Minnesota,1989;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理解性别差异:美国女性经济史》(Understanding the Gender Gap: An Economic History of American Women),Oxford,1999。
我也大量引用了共产主义研究群(Communist Research Cluster)的共产主义干预系列(Communist Interventions series)的三卷本,在网上可以查阅到。我对第三本《革命女权主义》的阅读尤其充实了这一论点。
[5] 塞科姆,《历尽艰辛》,第74页。
[6] 戈尔丁,《理解性别差异》,第48-49页。
[7] 同上。
[8] 同上;塞科姆,《历尽艰辛》。
[9] 马克思,《资本论》卷一,MECW 35,第465页。
[10] 同上注,第470页。
[11] 这段关于美国奴隶制下的性别政策的分析,以及下文引用的作者的段落,都要归功于霍滕斯 · 斯皮勒(Hortense Spillers)和赛蒂亚·哈特曼(Saidiya Hartman)的作品。
[12] 安吉拉·戴维斯,“对奴隶共同体中黑人女性角色的反思(Reflections on the Black Woman’s Role in the Community of Slavers)”,1972,见《美国的黑人革命者》(Black Revolutionaries in the United States),《共产主义干预》,第二册,共产主义研究群编辑(下文简称CRC 2),第329-330页。
[13] 杜波依斯,《黑人的重建》(Black Reconstruction),CRC 2,第7页。
[14] 安吉拉·戴维斯,“对奴隶共同体中黑人女性角色的反思”,1972,CRC 2,第332-333页。
[15]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ECW 6,第501页。
[16] 同上注,第505页。《宣言》中废除继承权的要求是对资产阶级家庭的挑战,而不是像当时其他一些社会主义者设想的那样,足以取代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消灭。在其他一些地方,马克思对于从完整的共产主义纲领中抽离出来的取消继承权的要求的态度是比较含糊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这一要求写进了1848年的《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MECW 7,第4页)中。在1869年国际工人协会上的一次演讲中,他明确表示,在不消灭资本主义剥削的情况下消灭遗产本身“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是反动的。我们在考察继承法时,必然要假定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继续存在。”(MECW 21,第66页)。有人猜测马克思也担心这种要求可能会疏远农民(MECW 26,“序言”第二十四页)。
[17] 恩格斯,《家庭,私有财产与国家的起源》(Origins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1884年,见《革命的女权主义》,《共产主义干预》卷3,共产主义研究群编辑(下文简称CRC 3),第18页。
[18] 同上,第19页。
[19] 同上,第15页。
[20] 同上,第19页。
[21] 恩格斯致马克思的信,1869年6月22日,MECW 43,第295页。
[22] 这里用的“酷儿”一词涵盖了对性和性别偏异、性自由和非规范的性愉悦的多种形式的捍卫与追求。酷儿的生活经常体现于组织密集的反文化中,且经常被描述为一定程度上有自我意识的政治项目。这篇研究主要感兴趣的是渗透在边缘无产者的生存和反抗中的酷儿形式。酷儿爱的普遍化,是对非压迫性关怀的转变和普遍化。
[23] 傅立叶,引自马克思《神圣家族》,MECW 4,第196页。
[24] 傅立叶,《四种运动的理论》(The Theory of the Four Movements),Gareth Stedman Jones和Ian Patterson编,Cambridge,1996,第111页。
[25] 傅立叶,《夏尔·傅立叶的乌托邦设想》(The Utopian Vision of Charles Fourier),Jonathan Beecher和Richard Bienvenu编,Beacon,1972,第346页。
[26] 克里斯·奇蒂,未发表的论文草稿,由Max Fox提供。
[27] 芬妮(Fanny)和史黛拉(Stella)是两名在伦敦被捕、拘留的变装者(Mary-Anns)。他们在河岸街剧院用“叽叽喳喳的声音”嘲笑去剧院的人,可能还卖淫,扰乱了秩序。他们的变装癖是无可否认的,但法院医生也对他们女性般的皮肤和体格感到吃惊;检查身体时,六个医生趁机轮流用手指插他们的肛门。尼尔·麦肯纳(Neil McKenna),《芬妮与史黛拉:震惊维多利亚英国的两个年轻男子》,Faber,2013。对妓院数量的估计来自麦肯纳。
[28] 茱蒂丝·沃克维奇(Judith Walkowitz),《卖淫与维多利亚社会》,Cambridge,1982。
[29] 凯瑟琳·弗兰克(Katherine Franke),《婚姻:婚姻平等的危机》(Wedlocked: The Perils of Marriage Equality)
[30] 【译注】这是文化和文学理论语境的术语,指某个已有的概念以不同的形式或在不同的语境下被重新建立,但是与传统版本相比又没有激进的变化,除非是越轨的再记认(见A Dictionary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31] 这篇文章大体上是按照“一部分离的历史”的批判思路理解工人运动的。
[32] 这里,理解男性养家糊口范式的巩固的主要参考文献是塞科姆的《历尽艰辛》。另外参见1980年代初以来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关于“家庭工资”的争论,包括海蒂·哈特曼(Heidi Hartmann),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in Women and Revolution, ed. by Lydia Sargent (Black Rose 1981); 米歇尔·巴雷特和玛利亚·拉马斯(Michéle Barrett), Women’s Oppression Today: The Marxist / Feminist Encounter (Verso, 1980); 乔安娜·布伦纳和(Johanna Brenner and Maria Ramas), ‘Rethinking Women’s Oppression’ New Left Review I / 144 (1984); 以及玛撒·梅(Martha May)的 ‘The Historical Problem of the Family Wage’ Feminist Studies, 8 / 2 (1982). 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参与度数据见戈尔丁, Understanding the Gender Gap.
[33] 我暂且不讨论顺性别女性的生育能力对巩固劳动的性别化分工有何影响,这是布伦纳(Brenner)和拉马斯(Ramas)论证的特别焦点,我们有机会将密切留意。
[34] 戈尔丁,《理解性别差异》,第45页。
[35] 共产主义研究群,《欧洲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干预》第一册(下文简称CRC 1),第24-25页。
[36] 罗莎·卢森堡,“妇女选举权和阶级斗争”,1912年,CRC 3,第57页。
[37] 克拉拉·柴特金,“只有与无产阶级女性结合,社会主义才能取胜”,1896年,CRC 3,第51页。
[38] 琼·斯科特(Joan W. Scott)与路易丝·蒂莉(Louise A. Tilly),“19世纪欧洲女性的工作与家庭”(Women’s Work and the Family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社会与历史比较文学研究》(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第17期,1,1975年,第64页。
[39] 亚历山德拉·柯伦泰,“论婚姻关系领域中的共产主义道德(Theses on Communist Morality in the Sphere of Marital Relations)”,1921年,CRR 1,212年。
[40] 柯伦泰,“共产主义与家庭(Communism and the Family)”,1920年,CRC 3,第96页。
[41] 同上,第97页。
[42] 同上。
[43] 引自斯科特,“勺子的暴政”(Tyranny of the Ladle),《伦敦书评》(London Review of Books),第34期,23,2012年,第6页。
[44] 同上。【译注】该话出自时任甘肃第一书记汪峰给毛泽东写的信,引自宋永毅,“再论粮食战争:军事共产主义和中国大饥荒的发生”,《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14年2月号,64页。
[45] 在那些由于棉铃象鼻虫灾害而突然切换到雇佣劳动制农业的南部地区,黑人的结婚率也下降了。布鲁姆(Bloom),费根鲍姆(Feigenbaum)和穆勒(Muller),“1892-1930年间的租佃,婚姻与棉铃象鼻虫泛滥(Tenancy, Marriage, and the Boll Weevil Infestation, 1892-1930)”,《人口志》(Demography),第54期,3,2017年。
[46] 阿兰·贝鲁布(Allan Bérubé),《在战火下出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男女同性恋史》(Coming Out Under Fire: The History of Gay Men and Women in World War Two),Free Press,2000年。
[47] 【译注】工合全称工业合作社。抗日战争时期,美国海军陆战队少校卡尔逊(Evans Carlson)受到八路军的表现影响,提倡官兵应打成一团,为共同理念而奋斗,并称这种做法为“工合”。1943年的电影《工合!》(又名《喋血马金岛》)上映后,该词开始在美国社会流行,脱离了字面意义而专指“奋勇向前”甚至“过分热情”的精神。
[48] 2001年6月西维亚·雷·里维拉在纽约的同性恋社区服务中心(Lesbian and Gay Community Services Center)做的演讲。
[49] 【译注】气象员,全称地下气象组织(Weather Underground Organization),名字出自鲍伯·戴伦(Bob Dylan)的“地下乡愁布鲁斯”一歌(Subterranean Homesick Blues),是1969年开始活跃的反越战极左组织,1970年发表“战争状态宣言”,目标是建立革命政党和推翻美帝,越战结束后开始式微,1977年停止运作。乔治·杰克逊旅,名字出自1971年据称越狱时被枪杀的黑豹党成员乔治·杰克逊,1975年开始活跃,曾参与一系列针对政府和企业的炸弹等袭击,目标是武力推翻美国政府,建立集体领导,76和77年成员相继被捕。
[50] 见“地下气象员运动中的女性(Women of the Weather Underground)”,“给女性运动的一封集体信”(A Collective Letter to the Women’s Movement),CRC 3,第160页。
[51] 艾莉森·爱德华兹(Alison Edwards),“强奸,种族主义与白人女性运动(Rape, Racism, and the White Women’s Movemet)”,1976年,CRC 3,第228页。
[52] 第三世界同性恋革命运动,“16项政纲与计划”(16 Point Platform and Program),《出柜!》(Come Out!)第7期,1970年。最近发表于Pinko,第1期,2019年。
[53] 贝蒂·弗里丹,《女性的奥秘》,Norton,1963,第15页。
[54] 第三世界女性联盟,“斗争中的妇女(Women in the Struggle)”,1971年,CRC 3,第254页。
[55] 对莫尼汉报告的更详尽的解读,见霍顿斯·斯皮勒(Hortense J. Spillers),“妈妈的宝贝,爸爸的也许:一本美国语法书(Mama’s Baby Papa’s Maybe: An American Grammar Book)”,Diacritics,第17期,2,1987年,第64-81页。
[56] 弗朗西斯·比尔,双重威胁:做黑人与做女性,1976年,CRC 3,第257页。
[57] 除了威尔逊·舍温(Wilson Sherwin)的一本未发表的著作以外,许多关于NWRO的历史研究都几乎完全忽视了该运动的这一维度。这里分析要归功于舍温的《丰富的需求:重温福利权力运动的激进政治》(Rich in Needs: Revisiting the Radical Politics of the Welfare Rights Movement),未发表的博士论文,CUNY,研究生中心,纽约,2019。
[58] 玛利亚罗莎·达拉·科斯特,“女性与社区的颠覆”,1972年,CRC 3,第283页。
[59] 同上,第282页。
[60] 同上,第286页。
[61] 同上,第288页。
[62] 西尔维娅·费代里奇,“工资对抗家务劳动(Wages Against Housework)”,1974年,CRC 1,第336页。
[63] 同上,第337页。
[64] 这里既把家务劳动工资运动看做一种反工作运动,也看做一种讽刺性的挑衅的态度,结合了凯茜·韦克斯(Kathi Weeks)的修正主义史学,见《工作的问题: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反工作政治与后工作的想象》(The Problem with Work: Feminism, Marxism, Antiwork Politics and Postwork Imaginaries),Duke,2001年,以及威尔逊·舍温和达拉·科斯特、费代里奇最近发表的一些不经意的评论。
[65] TC,“无事生非(Much Ado About Nothing)”,《尾注》第1期。【译注】本文集没有收录。
[66] 见“一部分离的历史”。
[67] 埃斯特班·奥尔蒂斯·奥斯皮纳(Esteban Ortiz-Ospina)和桑德拉·茨维科娃(Sandra Tzvetkova),“工作的女性: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的主要事实与倾向(Working Women: Key Facts and trends in femal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用数据看世界(Our World in Data),2017年。
[68] 同上。
[69] 约兰·特班(Göran Therborn),《在性与权力之间:1900-2000年间全世界的家庭》(Between Sex and Power: Family in the World 1900-2000),Routledge,2004年,第190页。
[70] 斯蒂芬妮·孔茨(Stephanie Coontz),“婚姻的世界历史性变迁(The World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of Marriage)”,婚姻与家庭杂志(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66,2004年,第974-979页。
[71] 约兰·特班,《在性与权力之间》,第293页。
[72] 同上,第199页。
[73] 当代的很多作者怀着新的批判热情再次讨论起家庭的消灭。JJ·格里森(JJ Gleeson)和KD·格里菲斯(KD Griffiths)在“儿童共产主义:21世纪家庭的女权主义分析与共产主义消灭家庭的提议(Kinderkommunismus: A Feminist Analysis of the 21st-Century Family and a Communist Proposal for its Abolition)”(Ritual,2015年)中,提议用“反二元的托儿所(‘the anti-dyadic crèche’)”作为“反家庭机构”的理想形式来满足代际再生产的社会需求,把所有形式的教育整合进去。然而格里森和格里菲斯在他们的“反家庭”计划中没有充分说明国家或雇佣劳动的作用。
索菲·刘易斯(Sophie Lewis)关于妊娠代孕的书中提出了一种 “妊娠公社(gestational commune)”,作为非所有式关怀关系的普遍化。刘易斯通过调查目前代孕工人的斗争,把基因关系、妊娠劳动和育儿区分并分离开,把妊娠与家庭繁衍的无工资劳动去自然化。索菲·刘易斯(Sophie Lewis),《现在就成全代孕:反家庭的女权主义》(Full Surrogacy Now: Feminism Against the Family),Verso,2019。
玛德琳·莱恩-麦金利(Madeline Lane-McKinley)在最近对消灭家庭的号召中,写到了集体相互依存的共同实践,她指出关怀的积极内核要被保护和改造:“终结作为私有财产单位的‘家庭’的革命性视野,如何动员我们迈向更全面、剥削更少的关怀的图景?这种对集体关怀的渴望必须与各类反家庭的言论齐头并进——否则便会落入自我管理和自律性的逻辑。玛德琳·莱恩-麦金利,“儿童的观念(The Idea of Children)”,Blind Field杂志(Blind Field Journal),2018年。
[74] 这一设想的详叙见ME O’Brien,“Communizing Care”,Pinko 第一期(2019)。